2025APP定制公司哪家专业,优质APP定制公司推荐10家
2025APP定制公司哪家专业,优质APP定制公司推荐10家
2025APP定制公司哪家专业,优质APP定制公司推荐10家作者:陶天野(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(shuòshì)研究生);虞鑫(yúxīn)[(通讯作者)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深圳大学全球(quánqiú)传播研究院研究员]
来源(láiyuán):《青年记者》2025年第4期
 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“一体化管理”进行(jìnxíng)定位,随后对其(qí)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。
进入新时代以来,信息技术迅猛发展,重塑媒体形态、舆论生态(shēngtài)、文化业态。面对(duì)技术变革和国家现代化建设(jiànshè)的时代要求,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,提出“深化网络(wǎngluò)(wǎngluò)管理体制改革,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,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的改革要求,作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[1]。如何理解“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”(以下简称“一体化管理”)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?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(jìnniánlái)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“一体化管理”进行定位(dìngwèi),随后对其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(fēnxī)。
《决定》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,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(zhòngdà)任务,包括(bāokuò)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,优化文化服务和(hé)文化产品供给机制,健全网络(wǎngluò)综合治理体系(tǐxì)(tǐxì),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。在这一政策语境下提出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举措,完成了从战略目标到实践路径的深层次推进。
从直接文本来看,“一体化管理”首先是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(tǐxì)的(de)(de)重要一环。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从“对互联网实行科学管理”的要求发展(fāzhǎn)而来,秉承“建设网络强国”的使命,强调多(duō)(duō)维度、多主体、多目标、多手段的治理过程,反映了中国互联网治理理念(lǐniàn)的进化[2]。“一体化管理”以整体性思维促进多主体协同,助力互联网治理的系统性谋划、综合性治理、体系化推进。习近平总书记(zǒngshūjì)主持召开中央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提出,要逐步建立起涵盖(hángài)领导管理、正(zhèng)能量(néngliàng)传播、内容管控、社会协同、网络法治(fǎzhì)、技术治网等各方面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。其中(qízhōng),正能量传播和内容管控已经传达了一体两面的内涵:“正能量传播的实质是正能量内容的生产,而内容管控则是针对违法与不良信息的管制”,二者相互结合交叉和补充,成为当前网络综合治理经验的初步凝练[3]。在此基础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强调整合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,在党和国家整体统筹之下协同推进正向引导与反向(fǎnxiàng)监管,意在明确综合治网职责边界,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、属地管理和主管(zhǔguǎn)主办责任,既从内容生产端发力创新宣传形式,也(yě)从传播管理端发力把控舆论全程,最终实现网络空间的全局优化,确保主流价值观在线上线下的统一传播和有效覆盖[4]。
从时间维度(wéidù)来看,“一体化管理”与加快建设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的(de)(de)任务相辅相成。全媒体传播体系是(shì)(shì)媒体融合在舆论(yúlùn)引导中的重要运用模式[5],党的政策文件多次强调,对于媒体融合,“正能量是总要求,管得住是硬道理,用得好是真本事”,“一个标准,一体管理”是让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重要保证,也(yě)是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提升正面宣传质量的必要手段。一方面,作为(zuòwéi)(wèi)一个多元主体共在的复合型生态系统,全媒体传播体系最重要的特征是“主体的集合性”,不同性质(xìngzhì)、类型的主体具有不同的立场(lìchǎng)、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[6],因而(yīnér)需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,配套落实政策措施,为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[7]。这与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内在逻辑(luójí)是一致的,“一体化管理”在深化(shēnhuà)网络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,也对新闻宣传工作机制提出要求,从而(cóngér)能够结合信息化发展成果助力传媒管理创新。另一方面,内容建设是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核心任务,而网络舆论是传播效果的重要评估依据(yījù),能够反映社会主要矛盾,为解决“好新闻如何传播”的问题提供认知资源,“一体化管理”有利于从思维和认知模式层面深化媒体融合,塑造更深入、更具说服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,为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提供支持。
从宏观格局来看,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最终服务于(yú)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。在2023年全国(quánguó)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,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,事关国家长治久安,事关民族凝聚力和(hé)向心力,是一项(yīxiàng)极端重要的工作”[8],并提出“七个着力”作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和行动指南。其中,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、着力建设(jiànshè)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着力提升新闻(xīnwén)舆论(yúlùn)传播(chuánbō)(chuánbō)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三点,分别是开展(kāizhǎn)新闻宣传文化工作的根本保证、总体方向(fāngxiàng)和实践路径[9],“一体化管理”承接和贯通这三方面要求,立足实践实际,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行动指示。具体而言,随着(suízhe)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、主战场(zhǔzhànchǎng),网络空间(wǎngluòkōngjiān)的舆论传播便成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。网络舆论传播可以分为“讲什么”和“如何(rúhé)讲”两个方面,前者要求通过网络综合治理来把握舆论方向,后者要求通过全媒体传播创新舆论方式[10],“一体化管理”以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坚持(jiānchí),统筹把握网络舆论传播的方向和方式,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中,通过网络空间综合治理,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,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提供助力。
整体(zhěngtǐ)来看,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新举措,“一体化管理”体现了(le)守正创新的思想方法,承接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使命,助力(zhùlì)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建立健全,为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,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文化条件。
解析概念内涵及生成原理,是社会科学研究的(de)(de)基本前提。在讨论如何推进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之前,应当结合对应的历史和现实语境,梳理“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”、“网络舆论(yúlùn)”、“一体化”这些次级概念的内涵和逻辑关系,解析“一体化管理”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来源,即回答“是什么”“为什么”的问题。
首先(shǒuxiān)考察“一体化管理”作为一项实践的(de)(de)指向对象——“新闻宣传”和“网络舆论”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关系。在“宣传”“新闻宣传”“舆论”“新闻舆论”等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各种话语表达中,这两个概念为何(wèihé)被专门提出,又为何能够并举、合为一体?通过话语分析方法,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常用话语进行历时性考察,可以理解其(qí)背后的观念发展变化(biànhuà)过程,透视“一体化管理”的理论内核。
在(zài)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和近代史发展历程双重影响下,中国新闻传播很长时间以来整体偏重“宣传”[11],中国共产党(zhōngguógòngchǎndǎng)的新闻宣传观念也首先建立在传统鼓动宣传的基础上,从而能(néng)促进共产主义(gòngchǎnzhǔyì)思想传播,推动党组织发展壮大(fāzhǎnzhuàngdà)[12]。从语言学角度看,“宣传”自建党以来便是最常出现的政策词汇,而“新闻工作(gōngzuò)”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开始作为(zuòwéi)一个独立语汇出现在重要文件中;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党的“新闻”和“宣传”工作始终紧密联系,不过更多(duō)的是一种工作理念而非语用(yǔyòng)概念,直到20世纪末,江泽民、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新闻宣传工作发表了(le)一系列讲话,“新闻宣传”概念才开始逐渐盛行,成为官方的统一称呼[13]。
改革开放后,理论界逐渐开始从“舆论(yúlùn)”视角(shìjiǎo)认识新闻宣传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,并(bìng)通过专门化、自觉(zìjué)化的(de)(de)(de)(de)理论和思想建构,来“协同新闻宣传与舆论监督这两种不同特性的信息传播形态”[14]。江泽民(jiāngzémín)同志在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中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“舆论导向”概念(gàiniàn),此后(cǐhòu)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”成为以(yǐ)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新闻思想;在此基础上,2002年起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“舆论引导”作为核心概念来强调,在舆论方向正确性的基础上,进一步提出对舆论工作的“水平”与“能力”的重视[15]。与此同时,随着21世纪社会转型带来多元社会思潮,互联网(hùliánwǎng)平台兴起成为社会言论的新容器(róngqì)和放大器,“网络舆论”“网上舆论”有关(yǒuguān)的生态学现象和对应概念逐步(zhúbù)进入政策制定者视野。2013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“8·19”讲话中指出,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,“舆论引导工作”逐步被单列出来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。2016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“新闻舆论”这一概念,指出新闻舆论工作的各个方面、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。过去常用的“新闻宣传工作”变成了“新闻舆论工作”,体现(tǐxiàn)出党对互联网时代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。这次会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转型的标志性里程碑。
综观这一过程可以发现,随着话语使用的变化,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不断成熟和发展,具体体现为对新闻规律(guīlǜ)不断探索、对舆论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越发重视。从“宣传”到“新闻宣传”的发展,是让新闻观念回归本位,承认新闻传播(chuánbō)活动有其规律,自觉适应和运用规律做工作;“舆论引导”和“网上舆论”等概念的出现,说明党对受众自身主体性的认识和尊重(zūnzhòng)。从“宣传”到“舆论”的话语变化实现了从单向传播到多向互动的理念进化,反映出“自下而上的意见(yìjiàn)流动(liúdòng)视角”,表明党的新闻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与时俱进的先进特征(tèzhēng)。
在这一背景下,“推进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与网络舆论(yúlùn)一体化管理”将“新闻宣传”和“网络舆论”两个概念并(bìng)置,首先顺应了(le)党的(de)(de)新闻宣传舆论话语的历史演变(yǎnbiàn)趋势,对新闻、宣传、舆论三者之间(zhījiān)的关系重新进行了科学认识和定位,是当前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立场和方法的直接反映。进一步地,前述(qiánshù)种种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(guānniàn)(guānniàn)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解释了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底层逻辑。杨保军认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(héxīn)观念有四个:党性原则(dǎngxìngyuánzé)(dǎngxìngyuánzé)观念、人民中心观念、新闻规律观念、正确舆论观念[16]。不难发现,尽管后两者与前两者之间存在概念层次上的差别,但四者本质上是统一的:“新闻规律观念”是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的必然要求,“正确舆论观念”是重要的方法论观念,二者通过指导具体实践把“党性原则观念”和“人民中心观念”落到实处;“党性原则观念”和“人民中心观念”经由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的理论论证而不可分割,在党性原则的统领下,新闻的人民性与党领导(lǐngdǎo)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(xíngchéng)互构关系,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社会意志的凝聚和统合,从而(cóngér)对“为了谁,依靠谁,我是谁”这个根本问题作出回应[17]。建立在上述这些观念内涵基础上、以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为内核(nèihé)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也就由此具备了深入推进互联网时代公意形成的可能性,这使得它与党的宣传思想保持内在一致并在逻辑上一脉相承,从而能够获得(huòdé)理论上的合法性。
如前所述,将网络舆论(yúlùn)①纳入考量是新时代党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(de)必然要求,体现了(le)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的基本立场,保证了“一体化管理(guǎnlǐ)”在理论层面(céngmiàn)的合法性。下面,通过考察网络舆论的发展历程和特点,可以(kěyǐ)进一步明确“一体化管理”提出的现实语境,理解其中包含的问题意识。换言之,当前网络舆论生态呈现出何种特征和影响,使得“一体化管理”成为深化改革的必要手段?
按照媒介(méijiè)技术(jìshù)演进过程,网络舆论发展历程可以被分为“00”年代(niándài)(niándài)、“10”年代和“20”年代三个阶段,经历了从“网络舆论”到“网络舆论生态”的认知变化(huà),与“媒介化社会”的建构(jiàngòu)过程呈现出相似的逻辑。不同的传播技术下舆论生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,也对舆论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,已有不少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,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。
第一,主流媒体不再是传统模式下强有力(qiángyǒulì)的传播主体,融合转型成为长期任务。这一趋势在(zài)(zài)21世纪初就已出现(chūxiàn),随着互联网(hùliánwǎng)进入Web2.0阶段,以网络为依托由普通民众生成和传播的“民间(mínjiān)舆论场(chǎng)”由弱到强,越来越显性化(xiǎnxìnghuà),开始对媒体议程产生影响。在早期“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”和“陕西华南虎造假事件”等社会事件中,都是网民先自发形成大范围讨论,随后引来国内传统媒体报道(méitǐbàodào)和有关部门调查介入[18]。2011年起,微博、微信(wēixìn)和客户端构成的“两微一端”新媒体传播矩阵成为网络舆论的主要载体,赋予公众“传受合一(héyī)”的身份(shēnfèn),这种与传统模式截然相反的议题生成次序越发常见。一项实证研究表明,传统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机制正在被颠覆,技术赋权之下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舆论热点往往先于媒体报道,能够(nénggòu)推动媒体关注并调整议题,舆论监督形式也逐渐(zhújiàn)从媒体监督转为全民监督[19]。对此,主流媒体倘若无法及时调整自身定位和传播模式,便很容易在“事件增多、议题拓展(tuòzhǎn)、传播主体多样”三重压力下陷入被动状态,甚至落入“塔西佗陷阱”[20]。
第二,网络舆论生态越发复杂,治理(zhìlǐ)手段亟须升级。虽然社交媒体上(shàng)公众(gōngzhòng)舆论的(de)(de)生成过程拓展了公众表达(biǎodá)权的实现途径,但表达便利与“海量意见”并不(bù)等同于舆论的发达[21]。按网络舆论的存在(cúnzài)形态来看,互联网(hùliánwǎng)(hùliánwǎng)空间的潜舆论显化、显舆论复杂化、行为舆论虚拟化(xūnǐhuà),构成“众声喧哗”的舆论环境,情绪因素在其中的影响越发突出,原本现实社会中以“清晰(qīngxī)的公开(gōngkāi)意见”为主要形态的舆论难以形成(xíngchéng)气候,反而导致谣言认同(rèntóng)、网络犬儒主义和民粹式政治等“信任异化”现象[22][23];按网络舆论的传播规则来看,互联网“去中心化”的背后往往是自由市场权力规则下的“再中心化”,简单来说即谁拥有的信息(xìnxī)最多、谁的信息更能吸引注意,谁便拥有话语权和主导议程的能力[24]。到2020年前后,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,以算法、算力和数据为核心要素的“机器”作为新的行动者参与到多重社交终端和场景的传播中,“技术—平台—政府”三者的博弈更加激烈,数据驱动的“复合型(fùhéxíng)舆论场”渐成气候,网络舆论集成了政府、企业、公众乃至技术、算法等多主体意见,导致“流动性过剩”,越发呈现出分散化、圈层化倾向,打破舆论生态的动态平衡[25]。
这两方面问题对应着我国新时代新闻舆论(yúlùn)工作的(de)(de)两个面向:一是从舆论引导(yǐndǎo)的视角出发,对主流媒体的环境适应力、民意反映力、舆论引导力提出要求(yāoqiú),加快推进媒体融合转型;二是从舆论治理的视角出发,观照(guānzhào)互联网场(chǎng)域内不同主体(zhǔtǐ)的话语表达、传播逻辑、互动关系,探索互联网治理有效模式。二者(èrzhě)相辅相成,本质上是统一的。随着技术发展,这两方面工作势必要求进一步贯通和融合,通过体制机制的全方位(quánfāngwèi)改革,实现构建网上网下一体(yītǐ)、内宣外宣(wàixuān)联动的主流舆论新格局的根本任务。“一体化管理”由此承接了“主流舆论场”构建和“复合型舆论场”治理的双重要求,内在地包含了正面宣传、舆论监督(yúlùnjiāndū)、舆论引导、网络空间净化等多方面行动内容,成为实现两个面向统一性的具体手段。此时“一体”指的是方法论上的一致性,即无论是哪(nǎ)方面的工作内容,都需要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确保执行层面多主体、多手段的协调性,体现了治理思维的综合意义,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党委领导、政府管理、企业履责、社会(shèhuì)监督、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”的综合治网格局两相呼应。
中国互联网治理(zhìlǐ)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相当的(de)同构性,正由政府主导的传统管理形式转向政府、市场(shìchǎng)、社会(shèhuì)多元主体等共同参与的形式[26]。在此背景下提出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当然也需适应这一发展态势。习近平总书记对综合治网格局的论述(lùnshù)已经指出了“一体”的总要求和“多元”趋势之间的整体关系,但二者在实践层面的协同性具体(jùtǐ)为何、如何能实现,尚需要进一步考察。
随着网络社会崛起,“媒介逻辑”超越“事实逻辑”成为(chéngwéi)社会运行的(de)(de)主导性力量,往往要求重构国家、社会、市场等的角色和关系,建立一种多元(duōyuán)主体共同参与和协作的模式,以对这种力量进行约束(yuēshù)。然而,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逻辑的方案中(zhōng),有关“多主体共治”的尝试总潜在地包含了“去国家化”的理论立场[27],并在现实中带来令人失望的结果:当“多主体”上升为某种“主义”,它非但无法解决媒介化政治的根本问题,还导致了全球性的“互联网分裂”(Splinternet)和网络治理的“民主赤字”[28],严重危害了新闻业(xīnwényè)的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。此时(cǐshí),重新引入政府(zhèngfǔ)的力量、将治理权力收归民族国家,反而又成为全球性的趋势[29]。
与此不同的(de)是,在中(zhōng)国互联网治理(zhìlǐ)历程(lìchéng)中,国家(guójiā)(guójiā)始终处于核心(héxīn)主导地位。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(lǐngdǎo)下的制度体系,党的领导贯穿治党与治国的全过程,通过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,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[30]。因而在推进网络治理现代化(xiàndàihuà)的过程中,党对新闻宣传和(hé)网络空间的领导一以贯之,且随着新媒体环境的发展(fāzhǎn)变化而不断加强。具体可以从“党管媒体”和“党管网络”的行动路径中理解这一点:“党管媒体”是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核心原则(yuánzé),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“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”,要求通过政策引导(yǐndǎo)和技术规制(guīzhì)确保正确舆论导向。党管媒体,不能说只管党办(bàn)的媒体,而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,这个领导不是“隔靴搔痒式”领导,而是全局性、根本性的领导,方式可以有区别,但不能让党管媒体的原则被架空;“无论时代如何(rúhé)发展、媒体格局如何变化,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”[31]。随着技术发展,这一管理思路逐步拓展到更广泛的互联网空间。2013年,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,提出推动传统媒体(chuántǒngméitǐ)和新兴(xīnxīng)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,同时指出(zhǐchū)要“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”、“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”,将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紧紧关联(guānlián)在一起[32]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党和政府陆续出台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(guīdìng)》、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等作为规制手段,重视、发展和治理信息技术(xìnxījìshù)成为新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。2018年,国务院下发《国务院关于机构(jīgòu)设置的通知(tōngzhī)》,指出国家网信(wǎngxìn)办与中央网信办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,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,从而理顺网信办和国新办的职能分工,使前者专注于网络内容监管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治理,后者侧重对外宣传和国际舆论引导,进一步确保党对网络空间的领导效能。
不过,不论国家力量是(shì)“重新出场(chūchǎng)”还是“始终在场”,治理理念和措施都(dōu)需要随着环境变化而相应地更新,否则会陷入“只有底线思维,没有理论辩论;只讲(jiǎng)安全意识,不讲治理方略”的桎梏。换言之,对具体(jùtǐ)手段和方式的考虑,始终是党的领导下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应有之义,也是保证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统一性的前提。此时,党的功能定位(gōngnéngdìngwèi)是“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”:既总揽全局,又(yòu)不包揽一切,充分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。
因此,如果将中国特色的(de)网络(wǎngluò)治理(zhìlǐ)模式概括为“一体多元(duōyuán)模式”:党(dǎng)委和(hé)政府居于核心,其他主体居于外围、不同程度参与其中(qízhōng),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构筑(gòuzhù)的“同心圆”治理结构[33],那么“一体化管理”便是基于这一结构提出的创新措施,它在(zài)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构建“一体”和“多元”关系,实现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两方面工作的有效结合,这意味着在制度上从新闻管理和网络管理“两套班子”进一步(jìnyíbù)转向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全过程的“穿透式监管”,把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、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纳入管理范围,提高党和政府对“同心圆”内不同主体的统筹效能;在理念上明确中国互联网治理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为首要目的,从“党管媒体”、“党管网络”的分别行动模式,转变(zhuǎnbiàn)为“党管意识形态”理念下的整体性工作逻辑,使各(gè)部门、各领域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。
“一体化管理”的(de)合法性(héfǎxìng)、必要性、有效性,论证了其作为政策概念何以(héyǐ)可能,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(jìnyíbù)聚焦现实行动路径(lùjìng),考察它作为改革方向何以可为。《决定》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为“六个坚持(jiānchí)”:坚持党的全面领导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、坚持守正创新、坚持以制度建设(jiànshè)为主线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、坚持系统观念。这六项原则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布局提供了根本遵循,在此基础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实践方针和实现路径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。
第一,以服务党和人民(rénmín)(rénmín)(dǎnghérénmín)为根本,坚持网络群众路线(qúnzhònglùxiàn)。“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”是奠定“一体化管理”话语合法性(héfǎxìng)的(de)(de)(de)理论基础,服务党和人民是“一体化管理”的根本使命。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,而政治的核心在于(yú)权力,权力的核心在于民意,要确保“一体化管理”有效落实,必须尊重人民主体(zhǔtǐ)(zhǔtǐ)地位和首创精神,做到“人民有所呼、改革有所应”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领导干部(gànbù)要学网、懂网、用网,了解群众所思所愿,收集好想法好建议,积极回应网民关切”。互联网为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新的实践场域和技术支持,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成为政府公信力提升的重要途径,建立有效的政务网络平台,能够(nénggòu)快速收集社情民意并应用于科学决策,让网络舆论所反映出的社情民意成为凝聚共识的助推(zhùtuī)力;“互联网+群众路线”下党群关系(dǎngqúnguānxì)的“主体间性”特征,也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,为实现新闻媒体、平台企业、社会组织、用户个人等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模式夯实合作基石[34][35]。此外,新闻媒体也应把握平台、载体、导向等多方面的平衡,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,在“大舆论场”中发挥正向引导作用[36]。一个鲜活的例子是,2022年4月15日至5月16日,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,鼓励广大人民群众通过(tōngguò)人民日报社、新华社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提出意见建议。活动(huódòng)前后,主流媒体开展了全过程全方位的广泛宣传(xuānchuán),网民热烈讨论并积极建言献策(jiànyánxiàncè),各平台征求意见页面(yèmiàn)总阅读量达6.6亿次,收集各类留言超过854.2万条(wàntiáo),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注脚(zhùjiǎo)。
第二,以媒介技术变革为动能,推动管理制度创新(chuàngxīn)。《决定》指出:“坚持守正创新,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,紧跟时代步伐,顺应实践(shíjiàn)发展,突出问题导向,在新的(de)(de)起点上推进(tuījìn)理论创新、实践创新、制度创新、文化(wénhuà)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。”守正创新是党(dǎng)(dǎng)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,创新是大势所趋,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,也是“一体化管理”的核心要义,关于“怎样守正创新”的问题,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“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”,“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,该改(gǎi)的坚决改,不该改的不改”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为充分激发信息技术在新闻(xīnwén)传播领域的潜力,党和政府制定了媒介融合相关政策,推动党的新闻事业深度融入国家信息化(xìnxīhuà)建设(jiànshè)和社会治理(zhìlǐ)进程,以《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“互联网+”行动的指导意见》为代表的系列政策文件,旨在建立与新闻舆论工作(gōngzuò)相适应的规制框架(kuāngjià),激发传媒业(chuánméiyè)的核心竞争力[37]。对于“一体化管理”而言,技术驱动的制度创新同样是第一要务(yàowù),一方面,用科学化、制度化的网络舆情预防疏导机制代替“应激式”“运动式”管理传统,用“引领型、混合型”政府工具代替“强制型”工具,政府内部职能部门应结合具体情境厘清权责边界、达成理念共识,同时加快落实配套性(pèitàoxìng)的供给侧改革措施,支持外部主体(如媒体机构、企业(qǐyè)等)探索更有效的协同模式[38];另一方面,优化中国特色的“代理式”监管策略[39],利用超级平台企业提供的技术、数据和服务驱动国家数字化转型(zhuǎnxíng),建立人工智能驱动的舆情监测和分析(fēnxī)平台,实时追踪(zhuīzōng)新闻传播效果和网络舆情走势,分析了解(liǎojiě)受众需求和传播效果,通过新闻宣传的及时补位和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,避免舆论真空和失控。
第三(dìsān),以自主知识生产为引领,完善协同治理机制(jīzhì)。党的二十届三中(zhōng)全会《决定》提出,构建中国(zhōngguó)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,是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方面,而知识体系中的理论观念必须依据一定的中介手段转化为实践观念,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力量(lìliàng)和(hé)影响。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(guǎnlǐ)”立足“一体多元”网络治理模式的要求,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机制为实践目标,已有不少学者就不同社会主体(zhǔtǐ)的参与形式提出建议,如鼓励公众自主甄别信息、运用技术手段优化内容(nèiróng)过滤、建立平台间的合作机制等[40]。这些建议建立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上:随着媒介生态变革,以往的新闻专业知识常识化,职业新闻主体之外(zhīwài)的多种(duōzhǒng)社会主体成为新闻知识体系的运用者、呈现者,在新闻传播环境中承担不同的身份和角色。但想要确保各方面新闻生产活动(huódòng)能在“同心圆”结构中运转起来,更关键(guānjiàn)的是控制主体(即负责(fùzé)新闻领导和管理活动的主体)对新闻知识的理解和运用,并关系到不同主体间认知共识的建立[41]。这样一种认知成果实际上是对新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生产、知识体系构建提出要求,比如中国语境下的“协同治理”不同于(bùtóngyú)西方以博弈论、多中心治理等为基础的概念(gàiniàn),它提倡“党委领导,政府负责,社会协同”的党政一体化机制,这在根本上源于中国政党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在“国家与社会”这组关系中的角色[42],也与马克思主义(mǎkèsīzhǔyì)新闻观的底层逻辑(luójí)相契。以此为逻辑起点、以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大问题为导向开展(kāizhǎn)新闻学研究,才能构建有指导意义的知识结构,促进(cùjìn)科学的制度建设。
推进新闻宣传(xuānchuán)和网络舆论(yúlùn)一体化管理,是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(de)新要求(yāoqiú),为进一步(jìnyíbù)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抓手。党的“十四五”规划(guīhuà)指出,新闻传播既是事业又(yòu)是产业,既是阵地又是市场,既要宣传理论又要治理舆论,必须牢固树立系统观念,坚持统筹兼顾(tǒngchóujiāngù)、全面推进,才能促进系统集成、协同高效,实现文化发展质量、结构、规模(guīmó)、速度、效益、安全相统一[43]。在改革思路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以系统观念为核心(héxīn)指导,突出整体性、协同性、系统性,通过传统媒体领域和新兴媒体领域在管理机制上的深度融合,形成从内容生产到舆论治理的全链条、全流程管理模式,为应对网络舆论场复杂生态、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提供支持。
“一体化管理”是“党管媒体(méitǐ)”原则在(zài)当前外部环境变局下的(de)(de)(de)重要适应性举措。“党管媒体”是中(zhōng)国新闻媒体凝聚社会公意的前提,随着互联网成为宣传思想工作(gōngzuò)的主阵地,一方面,“党管媒体”的客体和主体范畴不断扩大,管理主体不局限于党和政府宣传部门,所指对象也不仅仅是由党直接(zhíjiē)掌握的媒体;另一方面,传统的新闻舆论(yúlùn)(yúlùn)主客体界限逐渐模糊,并在新媒体传播的动态过程中互相转化和融合,此时“一体”是具有综合性思维、囊括多元(duōyuán)主体的“一体”。如习近平总书记在“8·19”讲话中指出的,“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,动员(dòngyuán)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,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、行业管理、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”。应当发挥新闻宣传和网络(wǎngluò)舆论的协调合作优势,动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“办(管)”好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、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主体,实现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补充[44]。
技术革命日新月异,对于“一体化管理(guǎnlǐ)”要(yào)“管什么”、“怎么管”问题的回答始终需要更新(gēngxīn)和调整。在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要求的过程中,应当以党的领导为(wèi)根本原则,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、求真务实,不断探索新闻舆论工作新方法、新手段(shǒuduàn);学界也应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逻辑起点、以国家重大问题为导向(dǎoxiàng)、以本土经验为原材料,通过知识生产、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学术价值(jiàzhí),共同促进中国(zhōngguó)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完善,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更加健全,文化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。
【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“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坚守新闻真实性的路径、机制(jīzhì)与方法研究(yánjiū)”(批准(pīzhǔn)号:21CXW001)、深圳大学科研启动(qǐdòng)经费课题“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研究”成果】
①需要指出的是,如今学界(xuéjiè)在讨论“舆论”时,基本默认是指以互联网为表达渠道的“网络舆论”,但事实上(shàng)(shàng),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,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直到(zhídào)2015年底才超过50%,具备表达多数人意见的数量(shùliàng)基础;这些网络言论(yánlùn)内部也并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共识(所谓“公意”)以形成真正意义(yìyì)上的“舆论”,因此本文所说的“网络舆论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理性概念,而是以现象和问题为导向的广义概念。
[1]中共中央关于(guānyú)进一步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推进(tuījìn)中国式现代化的(de)决定[EB/OL].(2024-07-21)[2025-01-25].http://www.news.cn/politics/20240721/cec09ea2bde840dfb99331c48ab5523a/c.html.
[2]周净泓.构建(gòujiàn)安全平衡(pínghéng)发展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[J].青年记者,2021(04):105-106.
[3]郭全中,李黎.网络综合治理体系:概念沿革、生成逻辑(luójí)与实践路径(lùjìng)[J].传媒观察,2023(07):104-111.
[4]张居永.全媒体(méitǐ)时代网络舆论(yúlùn)生态治理策略研究[J].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,2021(09):81-84.
[5]叶俊(yèjùn).重塑舆论中心:媒体融合在舆论引导中的(de)运用与创新[J].新闻爱好者,2023(06):21-26.
[6]杨保军(yángbǎojūn),樊攀.多元主体协同: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升级的主导方向[J].传媒观察,2024(01):57-67.
[7]罗昕,张瑾杰.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基本内涵、评价(píngjià)标准与建设路径(lùjìng)[J].中国编辑,2023(10):30-36+53.
[8]习近平(xíjìnpíng)对宣传(xuānchuán)思想文化(wénhuà)工作(gōngzuò)作出重要指示[EB/OL].(2023-10-08)[2025-01-25]. http://www.news.cn/politics/leaders/2023-10/08/c_1129904890.htm.
[9]韩喜平,杨羽川.新(xīn)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指南(zhǐnán):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[J].思想理论教育(jiàoyù),2023(11):4-10.
[10]杨志超.全媒体时代推进网络意识形态(yìshíxíngtài)安全治理论(lǐlùn)析[J].思想战线,2024,50(3):112-119.
[11]梅(méi)琼林,郭万盛.中国新闻(xīnwén)传播对宣传之偏重(piānzhòng)的文化探源[J].上海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7(01):88-94.
[12]叶俊.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概念的历史及其(jíqí)终结[J].全球传媒学刊,2016,3(4):97-109.
[13]秦绍德.新闻舆论(yúlùn)工作(gōngzuò)核心概念刍论[J].新闻大学,2021(12):1-10+120.
[14]董天策,陈彦蓉,石钰婧.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舆论工作核心理念创新的百年进程:基于观念(guānniàn)史的视角(shìjiǎo)[J].当代传播(chuánbō),2021(06):4-11+24.
[15]樊亚平,刘静.舆论宣传·舆论导向·舆论引导(yǐndǎo):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[J].兰州大学(lánzhōudàxué)学报(社会科学版(bǎn)),2011,39(4):6-13.
[16]杨保军.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(mǎkèsīzhǔyì)新闻(xīnwén)观的核心观念(guānniàn)及其基本关系[J].新闻大学,2017(04):18-25+40+146.
[17]虞鑫,刘钊宁.从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到人民性:媒体的两种不同(bùtóng)公意形成之路[J].当代传播,2023(01):37-43.
[18]黄浩宇(huánghàoyǔ),方兴东,王奔.中国网络舆论30年:从(cóng)内容驱动走向数据驱动[J].传媒观察,2023(10):34-40.
[19]郭淼,杨济遥.倒置的传导:反向议程设置(shèzhì)视角下被(bèi)遮蔽的舆论(yúlùn)沟:以唐山打人事件为例[J].新闻界,2023(10):52-63.
[20]奉盛岚.“两个舆论(yúlùn)场”的溯源、发展(fāzhǎn)与当代意义探究[J].新闻研究导刊,2023,14(22):83-85.
[21]周葆华.社会化媒体(méitǐ)时代的舆论研究:概念、议题(yìtí)与创新[J].南京社会科学,2014(01):115-122.
[22]陈力丹,林羽丰(línyǔfēng).再论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[J].社会科学战线(zhànxiàn),2015(11):174-179.
[23] 全燕.“后真相时代”社交网络的(de)信任异化(yìhuà)现象研究[J].南京社会科学,2017(07):112-119.
[24]谢金林.网络舆论(yúlùn)生态系统内在机理(jīlǐ)及其治理研究——以网络政治舆论为分析视角[J].上海行政学院学报(xuébào),2013,14(4):90-101.
[25] 靖鸣,白龙.智媒时代网络舆论生态的核心内涵(nèihán)、问题与破解(pòjiě)之道[J].青年记者,2022(18):20-23.
[26]张志安,吴涛(wútāo).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互联网治理[J].新疆师范大学(xīnjiāngshīfàndàxué)学报(xuébào)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15,36(5):73-77+2.
[27]虞鑫,兰旻.媒介治理:国家治理体系中(zhōng)的(de)媒介角色——反思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与政治(zhèngzhì)[J].当代传播,2020(06):34-38.
[29]张志安(zhāngzhìān),冉桢.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:路径、效果与特征[J].新闻(xīnwén)与写作,2022(05):57-69.
[30]蔡礼强(càilǐqiáng),张晓彤.党的领导与(yǔ)国家治理现代化:功能定位与实现方式[J].中国行政管理(guǎnlǐ),2023,39(10):14-20.
[31]朱清河(qīnghé).中国共产党“党管媒体”的历史回溯与未来(wèilái)展望[J].青年记者,2021(12):14-17.
[32]陈昌凤,杨依军.意识形态安全(ānquán)与党管(dǎngguǎn)媒体原则:中国媒体融合政策(zhèngcè)之形成与体系建构[J].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2015,37(11):26-33.
[33]方兴东,何可,钟祥铭,等.中国网络治理(zhìlǐ)30年:“一体多元(duōyuán)模式”的(de)演进历程与规律启示[J].传媒观察,2023(09):54-65.
[34]杨畅.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是政府公信力提升的(de)重要(zhòngyào)路径: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群众路线重要论述[J].湖南师范大学(húnánshīfàndàxué)社会科学学报,2022,51(6):26-31.
[35]邓岩(dèngyán).“互联网(hùliánwǎng)+群众路线”的内涵与践行进路:以社会资本为(wèi)分析视角[J].社会主义研究,2023(05):132-140.
[36]翟梦杰.大舆论场视域下网络新闻(wǎngluòxīnwén)评论(pínglùn)如何引导舆论[J].青年记者,2023(21):73-75.
[37]王仕勇.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(xīnwén)政策的创新发展:逻辑理路(lǐlù)、实践路径和基本特征(jīběntèzhēng)[J].新闻与传播研究,2024,31(9):19-31+126.
[38]任昌辉,巢乃鹏.我国(wǒguó)政府(zhèngfǔ)网络舆情综合治理创新路径研究:基于治理工具论(lùn)的分析视角[J].电子政务,2021(06):40-51.
[39]李小宇.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策略(cèlüè)结构(jiégòu)与演化研究[J].情报科学,2014,32(6):24-29.
[40]孙萍,刘瑞生.网络生态视角下社交(shèjiāo)媒体的内容管理(guǎnlǐ)探析(tànxī)[J].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2019,41(12):50-53.
[41]杨保军.当代(dāngdài)中国新闻学自主(zìzhǔ)知识体系的实践呈现方式[J].编辑之友,2024(08):5-13.
[42]景跃进.将(jiāng)政党带进来——国家与(yǔ)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[J].探索(tànsuǒ)与争鸣,2019(08):85-100+198.
[43]中共中央办公厅(zhōnggòngzhōngyāngbàngōngtīng)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(yìnfā)《“十四五”文化(wénhuà)发展(fāzhǎn)规划(guīhuà)》[EB/OL].(2022-08-16)[2025-01-28].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2022-08/16/content_5705612.htm.
[44]朱鸿军,王涛.全党办媒体: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(xiàquán)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(de)适配理论(lǐlùn)探索[J].新闻大学,2024(08):43-54+119.
陶天野,虞鑫.推进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和网络舆论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:政策定位、概念内涵(nèihán)和实践路径[J].青年记者,2025(04):13-20.
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“一体化管理”进行(jìnxíng)定位,随后对其(qí)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。
进入新时代以来,信息技术迅猛发展,重塑媒体形态、舆论生态(shēngtài)、文化业态。面对(duì)技术变革和国家现代化建设(jiànshè)的时代要求,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,提出“深化网络(wǎngluò)(wǎngluò)管理体制改革,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,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的改革要求,作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[1]。如何理解“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”(以下简称“一体化管理”)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?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(jìnniánlái)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“一体化管理”进行定位(dìngwèi),随后对其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(fēnxī)。
《决定》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,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(zhòngdà)任务,包括(bāokuò)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,优化文化服务和(hé)文化产品供给机制,健全网络(wǎngluò)综合治理体系(tǐxì)(tǐxì),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。在这一政策语境下提出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举措,完成了从战略目标到实践路径的深层次推进。
从直接文本来看,“一体化管理”首先是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(tǐxì)的(de)(de)重要一环。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从“对互联网实行科学管理”的要求发展(fāzhǎn)而来,秉承“建设网络强国”的使命,强调多(duō)(duō)维度、多主体、多目标、多手段的治理过程,反映了中国互联网治理理念(lǐniàn)的进化[2]。“一体化管理”以整体性思维促进多主体协同,助力互联网治理的系统性谋划、综合性治理、体系化推进。习近平总书记(zǒngshūjì)主持召开中央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提出,要逐步建立起涵盖(hángài)领导管理、正(zhèng)能量(néngliàng)传播、内容管控、社会协同、网络法治(fǎzhì)、技术治网等各方面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。其中(qízhōng),正能量传播和内容管控已经传达了一体两面的内涵:“正能量传播的实质是正能量内容的生产,而内容管控则是针对违法与不良信息的管制”,二者相互结合交叉和补充,成为当前网络综合治理经验的初步凝练[3]。在此基础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强调整合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,在党和国家整体统筹之下协同推进正向引导与反向(fǎnxiàng)监管,意在明确综合治网职责边界,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、属地管理和主管(zhǔguǎn)主办责任,既从内容生产端发力创新宣传形式,也(yě)从传播管理端发力把控舆论全程,最终实现网络空间的全局优化,确保主流价值观在线上线下的统一传播和有效覆盖[4]。
从时间维度(wéidù)来看,“一体化管理”与加快建设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的(de)(de)任务相辅相成。全媒体传播体系是(shì)(shì)媒体融合在舆论(yúlùn)引导中的重要运用模式[5],党的政策文件多次强调,对于媒体融合,“正能量是总要求,管得住是硬道理,用得好是真本事”,“一个标准,一体管理”是让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重要保证,也(yě)是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提升正面宣传质量的必要手段。一方面,作为(zuòwéi)(wèi)一个多元主体共在的复合型生态系统,全媒体传播体系最重要的特征是“主体的集合性”,不同性质(xìngzhì)、类型的主体具有不同的立场(lìchǎng)、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[6],因而(yīnér)需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,配套落实政策措施,为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[7]。这与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内在逻辑(luójí)是一致的,“一体化管理”在深化(shēnhuà)网络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,也对新闻宣传工作机制提出要求,从而(cóngér)能够结合信息化发展成果助力传媒管理创新。另一方面,内容建设是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核心任务,而网络舆论是传播效果的重要评估依据(yījù),能够反映社会主要矛盾,为解决“好新闻如何传播”的问题提供认知资源,“一体化管理”有利于从思维和认知模式层面深化媒体融合,塑造更深入、更具说服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,为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提供支持。
从宏观格局来看,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最终服务于(yú)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。在2023年全国(quánguó)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,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,事关国家长治久安,事关民族凝聚力和(hé)向心力,是一项(yīxiàng)极端重要的工作”[8],并提出“七个着力”作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和行动指南。其中,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、着力建设(jiànshè)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着力提升新闻(xīnwén)舆论(yúlùn)传播(chuánbō)(chuánbō)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三点,分别是开展(kāizhǎn)新闻宣传文化工作的根本保证、总体方向(fāngxiàng)和实践路径[9],“一体化管理”承接和贯通这三方面要求,立足实践实际,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行动指示。具体而言,随着(suízhe)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、主战场(zhǔzhànchǎng),网络空间(wǎngluòkōngjiān)的舆论传播便成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。网络舆论传播可以分为“讲什么”和“如何(rúhé)讲”两个方面,前者要求通过网络综合治理来把握舆论方向,后者要求通过全媒体传播创新舆论方式[10],“一体化管理”以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坚持(jiānchí),统筹把握网络舆论传播的方向和方式,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中,通过网络空间综合治理,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,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提供助力。
整体(zhěngtǐ)来看,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新举措,“一体化管理”体现了(le)守正创新的思想方法,承接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使命,助力(zhùlì)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建立健全,为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,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文化条件。
解析概念内涵及生成原理,是社会科学研究的(de)(de)基本前提。在讨论如何推进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之前,应当结合对应的历史和现实语境,梳理“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”、“网络舆论(yúlùn)”、“一体化”这些次级概念的内涵和逻辑关系,解析“一体化管理”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来源,即回答“是什么”“为什么”的问题。
首先(shǒuxiān)考察“一体化管理”作为一项实践的(de)(de)指向对象——“新闻宣传”和“网络舆论”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关系。在“宣传”“新闻宣传”“舆论”“新闻舆论”等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各种话语表达中,这两个概念为何(wèihé)被专门提出,又为何能够并举、合为一体?通过话语分析方法,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常用话语进行历时性考察,可以理解其(qí)背后的观念发展变化(biànhuà)过程,透视“一体化管理”的理论内核。
在(zài)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和近代史发展历程双重影响下,中国新闻传播很长时间以来整体偏重“宣传”[11],中国共产党(zhōngguógòngchǎndǎng)的新闻宣传观念也首先建立在传统鼓动宣传的基础上,从而能(néng)促进共产主义(gòngchǎnzhǔyì)思想传播,推动党组织发展壮大(fāzhǎnzhuàngdà)[12]。从语言学角度看,“宣传”自建党以来便是最常出现的政策词汇,而“新闻工作(gōngzuò)”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开始作为(zuòwéi)一个独立语汇出现在重要文件中;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党的“新闻”和“宣传”工作始终紧密联系,不过更多(duō)的是一种工作理念而非语用(yǔyòng)概念,直到20世纪末,江泽民、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新闻宣传工作发表了(le)一系列讲话,“新闻宣传”概念才开始逐渐盛行,成为官方的统一称呼[13]。
改革开放后,理论界逐渐开始从“舆论(yúlùn)”视角(shìjiǎo)认识新闻宣传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,并(bìng)通过专门化、自觉(zìjué)化的(de)(de)(de)(de)理论和思想建构,来“协同新闻宣传与舆论监督这两种不同特性的信息传播形态”[14]。江泽民(jiāngzémín)同志在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中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“舆论导向”概念(gàiniàn),此后(cǐhòu)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”成为以(yǐ)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新闻思想;在此基础上,2002年起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“舆论引导”作为核心概念来强调,在舆论方向正确性的基础上,进一步提出对舆论工作的“水平”与“能力”的重视[15]。与此同时,随着21世纪社会转型带来多元社会思潮,互联网(hùliánwǎng)平台兴起成为社会言论的新容器(róngqì)和放大器,“网络舆论”“网上舆论”有关(yǒuguān)的生态学现象和对应概念逐步(zhúbù)进入政策制定者视野。2013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“8·19”讲话中指出,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,“舆论引导工作”逐步被单列出来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。2016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“新闻舆论”这一概念,指出新闻舆论工作的各个方面、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。过去常用的“新闻宣传工作”变成了“新闻舆论工作”,体现(tǐxiàn)出党对互联网时代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。这次会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转型的标志性里程碑。
综观这一过程可以发现,随着话语使用的变化,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不断成熟和发展,具体体现为对新闻规律(guīlǜ)不断探索、对舆论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越发重视。从“宣传”到“新闻宣传”的发展,是让新闻观念回归本位,承认新闻传播(chuánbō)活动有其规律,自觉适应和运用规律做工作;“舆论引导”和“网上舆论”等概念的出现,说明党对受众自身主体性的认识和尊重(zūnzhòng)。从“宣传”到“舆论”的话语变化实现了从单向传播到多向互动的理念进化,反映出“自下而上的意见(yìjiàn)流动(liúdòng)视角”,表明党的新闻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与时俱进的先进特征(tèzhēng)。
在这一背景下,“推进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与网络舆论(yúlùn)一体化管理”将“新闻宣传”和“网络舆论”两个概念并(bìng)置,首先顺应了(le)党的(de)(de)新闻宣传舆论话语的历史演变(yǎnbiàn)趋势,对新闻、宣传、舆论三者之间(zhījiān)的关系重新进行了科学认识和定位,是当前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立场和方法的直接反映。进一步地,前述(qiánshù)种种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(guānniàn)(guānniàn)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解释了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底层逻辑。杨保军认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(héxīn)观念有四个:党性原则(dǎngxìngyuánzé)(dǎngxìngyuánzé)观念、人民中心观念、新闻规律观念、正确舆论观念[16]。不难发现,尽管后两者与前两者之间存在概念层次上的差别,但四者本质上是统一的:“新闻规律观念”是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的必然要求,“正确舆论观念”是重要的方法论观念,二者通过指导具体实践把“党性原则观念”和“人民中心观念”落到实处;“党性原则观念”和“人民中心观念”经由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的理论论证而不可分割,在党性原则的统领下,新闻的人民性与党领导(lǐngdǎo)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(xíngchéng)互构关系,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社会意志的凝聚和统合,从而(cóngér)对“为了谁,依靠谁,我是谁”这个根本问题作出回应[17]。建立在上述这些观念内涵基础上、以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为内核(nèihé)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也就由此具备了深入推进互联网时代公意形成的可能性,这使得它与党的宣传思想保持内在一致并在逻辑上一脉相承,从而能够获得(huòdé)理论上的合法性。
如前所述,将网络舆论(yúlùn)①纳入考量是新时代党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(de)必然要求,体现了(le)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的基本立场,保证了“一体化管理(guǎnlǐ)”在理论层面(céngmiàn)的合法性。下面,通过考察网络舆论的发展历程和特点,可以(kěyǐ)进一步明确“一体化管理”提出的现实语境,理解其中包含的问题意识。换言之,当前网络舆论生态呈现出何种特征和影响,使得“一体化管理”成为深化改革的必要手段?
按照媒介(méijiè)技术(jìshù)演进过程,网络舆论发展历程可以被分为“00”年代(niándài)(niándài)、“10”年代和“20”年代三个阶段,经历了从“网络舆论”到“网络舆论生态”的认知变化(huà),与“媒介化社会”的建构(jiàngòu)过程呈现出相似的逻辑。不同的传播技术下舆论生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,也对舆论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,已有不少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,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。
第一,主流媒体不再是传统模式下强有力(qiángyǒulì)的传播主体,融合转型成为长期任务。这一趋势在(zài)(zài)21世纪初就已出现(chūxiàn),随着互联网(hùliánwǎng)进入Web2.0阶段,以网络为依托由普通民众生成和传播的“民间(mínjiān)舆论场(chǎng)”由弱到强,越来越显性化(xiǎnxìnghuà),开始对媒体议程产生影响。在早期“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”和“陕西华南虎造假事件”等社会事件中,都是网民先自发形成大范围讨论,随后引来国内传统媒体报道(méitǐbàodào)和有关部门调查介入[18]。2011年起,微博、微信(wēixìn)和客户端构成的“两微一端”新媒体传播矩阵成为网络舆论的主要载体,赋予公众“传受合一(héyī)”的身份(shēnfèn),这种与传统模式截然相反的议题生成次序越发常见。一项实证研究表明,传统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机制正在被颠覆,技术赋权之下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舆论热点往往先于媒体报道,能够(nénggòu)推动媒体关注并调整议题,舆论监督形式也逐渐(zhújiàn)从媒体监督转为全民监督[19]。对此,主流媒体倘若无法及时调整自身定位和传播模式,便很容易在“事件增多、议题拓展(tuòzhǎn)、传播主体多样”三重压力下陷入被动状态,甚至落入“塔西佗陷阱”[20]。
第二,网络舆论生态越发复杂,治理(zhìlǐ)手段亟须升级。虽然社交媒体上(shàng)公众(gōngzhòng)舆论的(de)(de)生成过程拓展了公众表达(biǎodá)权的实现途径,但表达便利与“海量意见”并不(bù)等同于舆论的发达[21]。按网络舆论的存在(cúnzài)形态来看,互联网(hùliánwǎng)(hùliánwǎng)空间的潜舆论显化、显舆论复杂化、行为舆论虚拟化(xūnǐhuà),构成“众声喧哗”的舆论环境,情绪因素在其中的影响越发突出,原本现实社会中以“清晰(qīngxī)的公开(gōngkāi)意见”为主要形态的舆论难以形成(xíngchéng)气候,反而导致谣言认同(rèntóng)、网络犬儒主义和民粹式政治等“信任异化”现象[22][23];按网络舆论的传播规则来看,互联网“去中心化”的背后往往是自由市场权力规则下的“再中心化”,简单来说即谁拥有的信息(xìnxī)最多、谁的信息更能吸引注意,谁便拥有话语权和主导议程的能力[24]。到2020年前后,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,以算法、算力和数据为核心要素的“机器”作为新的行动者参与到多重社交终端和场景的传播中,“技术—平台—政府”三者的博弈更加激烈,数据驱动的“复合型(fùhéxíng)舆论场”渐成气候,网络舆论集成了政府、企业、公众乃至技术、算法等多主体意见,导致“流动性过剩”,越发呈现出分散化、圈层化倾向,打破舆论生态的动态平衡[25]。
这两方面问题对应着我国新时代新闻舆论(yúlùn)工作的(de)(de)两个面向:一是从舆论引导(yǐndǎo)的视角出发,对主流媒体的环境适应力、民意反映力、舆论引导力提出要求(yāoqiú),加快推进媒体融合转型;二是从舆论治理的视角出发,观照(guānzhào)互联网场(chǎng)域内不同主体(zhǔtǐ)的话语表达、传播逻辑、互动关系,探索互联网治理有效模式。二者(èrzhě)相辅相成,本质上是统一的。随着技术发展,这两方面工作势必要求进一步贯通和融合,通过体制机制的全方位(quánfāngwèi)改革,实现构建网上网下一体(yītǐ)、内宣外宣(wàixuān)联动的主流舆论新格局的根本任务。“一体化管理”由此承接了“主流舆论场”构建和“复合型舆论场”治理的双重要求,内在地包含了正面宣传、舆论监督(yúlùnjiāndū)、舆论引导、网络空间净化等多方面行动内容,成为实现两个面向统一性的具体手段。此时“一体”指的是方法论上的一致性,即无论是哪(nǎ)方面的工作内容,都需要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确保执行层面多主体、多手段的协调性,体现了治理思维的综合意义,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党委领导、政府管理、企业履责、社会(shèhuì)监督、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”的综合治网格局两相呼应。
中国互联网治理(zhìlǐ)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相当的(de)同构性,正由政府主导的传统管理形式转向政府、市场(shìchǎng)、社会(shèhuì)多元主体等共同参与的形式[26]。在此背景下提出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当然也需适应这一发展态势。习近平总书记对综合治网格局的论述(lùnshù)已经指出了“一体”的总要求和“多元”趋势之间的整体关系,但二者在实践层面的协同性具体(jùtǐ)为何、如何能实现,尚需要进一步考察。
随着网络社会崛起,“媒介逻辑”超越“事实逻辑”成为(chéngwéi)社会运行的(de)(de)主导性力量,往往要求重构国家、社会、市场等的角色和关系,建立一种多元(duōyuán)主体共同参与和协作的模式,以对这种力量进行约束(yuēshù)。然而,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逻辑的方案中(zhōng),有关“多主体共治”的尝试总潜在地包含了“去国家化”的理论立场[27],并在现实中带来令人失望的结果:当“多主体”上升为某种“主义”,它非但无法解决媒介化政治的根本问题,还导致了全球性的“互联网分裂”(Splinternet)和网络治理的“民主赤字”[28],严重危害了新闻业(xīnwényè)的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。此时(cǐshí),重新引入政府(zhèngfǔ)的力量、将治理权力收归民族国家,反而又成为全球性的趋势[29]。
与此不同的(de)是,在中(zhōng)国互联网治理(zhìlǐ)历程(lìchéng)中,国家(guójiā)(guójiā)始终处于核心(héxīn)主导地位。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(lǐngdǎo)下的制度体系,党的领导贯穿治党与治国的全过程,通过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,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[30]。因而在推进网络治理现代化(xiàndàihuà)的过程中,党对新闻宣传和(hé)网络空间的领导一以贯之,且随着新媒体环境的发展(fāzhǎn)变化而不断加强。具体可以从“党管媒体”和“党管网络”的行动路径中理解这一点:“党管媒体”是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核心原则(yuánzé),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“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”,要求通过政策引导(yǐndǎo)和技术规制(guīzhì)确保正确舆论导向。党管媒体,不能说只管党办(bàn)的媒体,而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,这个领导不是“隔靴搔痒式”领导,而是全局性、根本性的领导,方式可以有区别,但不能让党管媒体的原则被架空;“无论时代如何(rúhé)发展、媒体格局如何变化,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”[31]。随着技术发展,这一管理思路逐步拓展到更广泛的互联网空间。2013年,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,提出推动传统媒体(chuántǒngméitǐ)和新兴(xīnxīng)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,同时指出(zhǐchū)要“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”、“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”,将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紧紧关联(guānlián)在一起[32]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党和政府陆续出台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(guīdìng)》、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等作为规制手段,重视、发展和治理信息技术(xìnxījìshù)成为新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。2018年,国务院下发《国务院关于机构(jīgòu)设置的通知(tōngzhī)》,指出国家网信(wǎngxìn)办与中央网信办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,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,从而理顺网信办和国新办的职能分工,使前者专注于网络内容监管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治理,后者侧重对外宣传和国际舆论引导,进一步确保党对网络空间的领导效能。
不过,不论国家力量是(shì)“重新出场(chūchǎng)”还是“始终在场”,治理理念和措施都(dōu)需要随着环境变化而相应地更新,否则会陷入“只有底线思维,没有理论辩论;只讲(jiǎng)安全意识,不讲治理方略”的桎梏。换言之,对具体(jùtǐ)手段和方式的考虑,始终是党的领导下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应有之义,也是保证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统一性的前提。此时,党的功能定位(gōngnéngdìngwèi)是“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”:既总揽全局,又(yòu)不包揽一切,充分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。
因此,如果将中国特色的(de)网络(wǎngluò)治理(zhìlǐ)模式概括为“一体多元(duōyuán)模式”:党(dǎng)委和(hé)政府居于核心,其他主体居于外围、不同程度参与其中(qízhōng),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构筑(gòuzhù)的“同心圆”治理结构[33],那么“一体化管理”便是基于这一结构提出的创新措施,它在(zài)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构建“一体”和“多元”关系,实现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两方面工作的有效结合,这意味着在制度上从新闻管理和网络管理“两套班子”进一步(jìnyíbù)转向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全过程的“穿透式监管”,把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、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纳入管理范围,提高党和政府对“同心圆”内不同主体的统筹效能;在理念上明确中国互联网治理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为首要目的,从“党管媒体”、“党管网络”的分别行动模式,转变(zhuǎnbiàn)为“党管意识形态”理念下的整体性工作逻辑,使各(gè)部门、各领域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。
“一体化管理”的(de)合法性(héfǎxìng)、必要性、有效性,论证了其作为政策概念何以(héyǐ)可能,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(jìnyíbù)聚焦现实行动路径(lùjìng),考察它作为改革方向何以可为。《决定》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为“六个坚持(jiānchí)”:坚持党的全面领导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、坚持守正创新、坚持以制度建设(jiànshè)为主线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、坚持系统观念。这六项原则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布局提供了根本遵循,在此基础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实践方针和实现路径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。
第一,以服务党和人民(rénmín)(rénmín)(dǎnghérénmín)为根本,坚持网络群众路线(qúnzhònglùxiàn)。“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”是奠定“一体化管理”话语合法性(héfǎxìng)的(de)(de)(de)理论基础,服务党和人民是“一体化管理”的根本使命。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,而政治的核心在于(yú)权力,权力的核心在于民意,要确保“一体化管理”有效落实,必须尊重人民主体(zhǔtǐ)(zhǔtǐ)地位和首创精神,做到“人民有所呼、改革有所应”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领导干部(gànbù)要学网、懂网、用网,了解群众所思所愿,收集好想法好建议,积极回应网民关切”。互联网为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新的实践场域和技术支持,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成为政府公信力提升的重要途径,建立有效的政务网络平台,能够(nénggòu)快速收集社情民意并应用于科学决策,让网络舆论所反映出的社情民意成为凝聚共识的助推(zhùtuī)力;“互联网+群众路线”下党群关系(dǎngqúnguānxì)的“主体间性”特征,也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,为实现新闻媒体、平台企业、社会组织、用户个人等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模式夯实合作基石[34][35]。此外,新闻媒体也应把握平台、载体、导向等多方面的平衡,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,在“大舆论场”中发挥正向引导作用[36]。一个鲜活的例子是,2022年4月15日至5月16日,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,鼓励广大人民群众通过(tōngguò)人民日报社、新华社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提出意见建议。活动(huódòng)前后,主流媒体开展了全过程全方位的广泛宣传(xuānchuán),网民热烈讨论并积极建言献策(jiànyánxiàncè),各平台征求意见页面(yèmiàn)总阅读量达6.6亿次,收集各类留言超过854.2万条(wàntiáo),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注脚(zhùjiǎo)。
第二,以媒介技术变革为动能,推动管理制度创新(chuàngxīn)。《决定》指出:“坚持守正创新,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,紧跟时代步伐,顺应实践(shíjiàn)发展,突出问题导向,在新的(de)(de)起点上推进(tuījìn)理论创新、实践创新、制度创新、文化(wénhuà)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。”守正创新是党(dǎng)(dǎng)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,创新是大势所趋,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,也是“一体化管理”的核心要义,关于“怎样守正创新”的问题,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“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”,“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,该改(gǎi)的坚决改,不该改的不改”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为充分激发信息技术在新闻(xīnwén)传播领域的潜力,党和政府制定了媒介融合相关政策,推动党的新闻事业深度融入国家信息化(xìnxīhuà)建设(jiànshè)和社会治理(zhìlǐ)进程,以《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“互联网+”行动的指导意见》为代表的系列政策文件,旨在建立与新闻舆论工作(gōngzuò)相适应的规制框架(kuāngjià),激发传媒业(chuánméiyè)的核心竞争力[37]。对于“一体化管理”而言,技术驱动的制度创新同样是第一要务(yàowù),一方面,用科学化、制度化的网络舆情预防疏导机制代替“应激式”“运动式”管理传统,用“引领型、混合型”政府工具代替“强制型”工具,政府内部职能部门应结合具体情境厘清权责边界、达成理念共识,同时加快落实配套性(pèitàoxìng)的供给侧改革措施,支持外部主体(如媒体机构、企业(qǐyè)等)探索更有效的协同模式[38];另一方面,优化中国特色的“代理式”监管策略[39],利用超级平台企业提供的技术、数据和服务驱动国家数字化转型(zhuǎnxíng),建立人工智能驱动的舆情监测和分析(fēnxī)平台,实时追踪(zhuīzōng)新闻传播效果和网络舆情走势,分析了解(liǎojiě)受众需求和传播效果,通过新闻宣传的及时补位和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,避免舆论真空和失控。
第三(dìsān),以自主知识生产为引领,完善协同治理机制(jīzhì)。党的二十届三中(zhōng)全会《决定》提出,构建中国(zhōngguó)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,是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方面,而知识体系中的理论观念必须依据一定的中介手段转化为实践观念,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力量(lìliàng)和(hé)影响。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(guǎnlǐ)”立足“一体多元”网络治理模式的要求,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机制为实践目标,已有不少学者就不同社会主体(zhǔtǐ)的参与形式提出建议,如鼓励公众自主甄别信息、运用技术手段优化内容(nèiróng)过滤、建立平台间的合作机制等[40]。这些建议建立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上:随着媒介生态变革,以往的新闻专业知识常识化,职业新闻主体之外(zhīwài)的多种(duōzhǒng)社会主体成为新闻知识体系的运用者、呈现者,在新闻传播环境中承担不同的身份和角色。但想要确保各方面新闻生产活动(huódòng)能在“同心圆”结构中运转起来,更关键(guānjiàn)的是控制主体(即负责(fùzé)新闻领导和管理活动的主体)对新闻知识的理解和运用,并关系到不同主体间认知共识的建立[41]。这样一种认知成果实际上是对新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生产、知识体系构建提出要求,比如中国语境下的“协同治理”不同于(bùtóngyú)西方以博弈论、多中心治理等为基础的概念(gàiniàn),它提倡“党委领导,政府负责,社会协同”的党政一体化机制,这在根本上源于中国政党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在“国家与社会”这组关系中的角色[42],也与马克思主义(mǎkèsīzhǔyì)新闻观的底层逻辑(luójí)相契。以此为逻辑起点、以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大问题为导向开展(kāizhǎn)新闻学研究,才能构建有指导意义的知识结构,促进(cùjìn)科学的制度建设。
推进新闻宣传(xuānchuán)和网络舆论(yúlùn)一体化管理,是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(de)新要求(yāoqiú),为进一步(jìnyíbù)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抓手。党的“十四五”规划(guīhuà)指出,新闻传播既是事业又(yòu)是产业,既是阵地又是市场,既要宣传理论又要治理舆论,必须牢固树立系统观念,坚持统筹兼顾(tǒngchóujiāngù)、全面推进,才能促进系统集成、协同高效,实现文化发展质量、结构、规模(guīmó)、速度、效益、安全相统一[43]。在改革思路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以系统观念为核心(héxīn)指导,突出整体性、协同性、系统性,通过传统媒体领域和新兴媒体领域在管理机制上的深度融合,形成从内容生产到舆论治理的全链条、全流程管理模式,为应对网络舆论场复杂生态、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提供支持。
“一体化管理”是“党管媒体(méitǐ)”原则在(zài)当前外部环境变局下的(de)(de)(de)重要适应性举措。“党管媒体”是中(zhōng)国新闻媒体凝聚社会公意的前提,随着互联网成为宣传思想工作(gōngzuò)的主阵地,一方面,“党管媒体”的客体和主体范畴不断扩大,管理主体不局限于党和政府宣传部门,所指对象也不仅仅是由党直接(zhíjiē)掌握的媒体;另一方面,传统的新闻舆论(yúlùn)(yúlùn)主客体界限逐渐模糊,并在新媒体传播的动态过程中互相转化和融合,此时“一体”是具有综合性思维、囊括多元(duōyuán)主体的“一体”。如习近平总书记在“8·19”讲话中指出的,“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,动员(dòngyuán)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,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、行业管理、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”。应当发挥新闻宣传和网络(wǎngluò)舆论的协调合作优势,动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“办(管)”好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、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主体,实现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补充[44]。
技术革命日新月异,对于“一体化管理(guǎnlǐ)”要(yào)“管什么”、“怎么管”问题的回答始终需要更新(gēngxīn)和调整。在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要求的过程中,应当以党的领导为(wèi)根本原则,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、求真务实,不断探索新闻舆论工作新方法、新手段(shǒuduàn);学界也应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逻辑起点、以国家重大问题为导向(dǎoxiàng)、以本土经验为原材料,通过知识生产、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学术价值(jiàzhí),共同促进中国(zhōngguó)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完善,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更加健全,文化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。
【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“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坚守新闻真实性的路径、机制(jīzhì)与方法研究(yánjiū)”(批准(pīzhǔn)号:21CXW001)、深圳大学科研启动(qǐdòng)经费课题“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研究”成果】
①需要指出的是,如今学界(xuéjiè)在讨论“舆论”时,基本默认是指以互联网为表达渠道的“网络舆论”,但事实上(shàng)(shàng),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,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直到(zhídào)2015年底才超过50%,具备表达多数人意见的数量(shùliàng)基础;这些网络言论(yánlùn)内部也并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共识(所谓“公意”)以形成真正意义(yìyì)上的“舆论”,因此本文所说的“网络舆论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理性概念,而是以现象和问题为导向的广义概念。
[1]中共中央关于(guānyú)进一步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推进(tuījìn)中国式现代化的(de)决定[EB/OL].(2024-07-21)[2025-01-25].http://www.news.cn/politics/20240721/cec09ea2bde840dfb99331c48ab5523a/c.html.
[2]周净泓.构建(gòujiàn)安全平衡(pínghéng)发展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[J].青年记者,2021(04):105-106.
[3]郭全中,李黎.网络综合治理体系:概念沿革、生成逻辑(luójí)与实践路径(lùjìng)[J].传媒观察,2023(07):104-111.
[4]张居永.全媒体(méitǐ)时代网络舆论(yúlùn)生态治理策略研究[J].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,2021(09):81-84.
[5]叶俊(yèjùn).重塑舆论中心:媒体融合在舆论引导中的(de)运用与创新[J].新闻爱好者,2023(06):21-26.
[6]杨保军(yángbǎojūn),樊攀.多元主体协同: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升级的主导方向[J].传媒观察,2024(01):57-67.
[7]罗昕,张瑾杰.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基本内涵、评价(píngjià)标准与建设路径(lùjìng)[J].中国编辑,2023(10):30-36+53.
[8]习近平(xíjìnpíng)对宣传(xuānchuán)思想文化(wénhuà)工作(gōngzuò)作出重要指示[EB/OL].(2023-10-08)[2025-01-25]. http://www.news.cn/politics/leaders/2023-10/08/c_1129904890.htm.
[9]韩喜平,杨羽川.新(xīn)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指南(zhǐnán):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[J].思想理论教育(jiàoyù),2023(11):4-10.
[10]杨志超.全媒体时代推进网络意识形态(yìshíxíngtài)安全治理论(lǐlùn)析[J].思想战线,2024,50(3):112-119.
[11]梅(méi)琼林,郭万盛.中国新闻(xīnwén)传播对宣传之偏重(piānzhòng)的文化探源[J].上海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7(01):88-94.
[12]叶俊.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概念的历史及其(jíqí)终结[J].全球传媒学刊,2016,3(4):97-109.
[13]秦绍德.新闻舆论(yúlùn)工作(gōngzuò)核心概念刍论[J].新闻大学,2021(12):1-10+120.
[14]董天策,陈彦蓉,石钰婧.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舆论工作核心理念创新的百年进程:基于观念(guānniàn)史的视角(shìjiǎo)[J].当代传播(chuánbō),2021(06):4-11+24.
[15]樊亚平,刘静.舆论宣传·舆论导向·舆论引导(yǐndǎo):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[J].兰州大学(lánzhōudàxué)学报(社会科学版(bǎn)),2011,39(4):6-13.
[16]杨保军.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(mǎkèsīzhǔyì)新闻(xīnwén)观的核心观念(guānniàn)及其基本关系[J].新闻大学,2017(04):18-25+40+146.
[17]虞鑫,刘钊宁.从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到人民性:媒体的两种不同(bùtóng)公意形成之路[J].当代传播,2023(01):37-43.
[18]黄浩宇(huánghàoyǔ),方兴东,王奔.中国网络舆论30年:从(cóng)内容驱动走向数据驱动[J].传媒观察,2023(10):34-40.
[19]郭淼,杨济遥.倒置的传导:反向议程设置(shèzhì)视角下被(bèi)遮蔽的舆论(yúlùn)沟:以唐山打人事件为例[J].新闻界,2023(10):52-63.
[20]奉盛岚.“两个舆论(yúlùn)场”的溯源、发展(fāzhǎn)与当代意义探究[J].新闻研究导刊,2023,14(22):83-85.
[21]周葆华.社会化媒体(méitǐ)时代的舆论研究:概念、议题(yìtí)与创新[J].南京社会科学,2014(01):115-122.
[22]陈力丹,林羽丰(línyǔfēng).再论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[J].社会科学战线(zhànxiàn),2015(11):174-179.
[23] 全燕.“后真相时代”社交网络的(de)信任异化(yìhuà)现象研究[J].南京社会科学,2017(07):112-119.
[24]谢金林.网络舆论(yúlùn)生态系统内在机理(jīlǐ)及其治理研究——以网络政治舆论为分析视角[J].上海行政学院学报(xuébào),2013,14(4):90-101.
[25] 靖鸣,白龙.智媒时代网络舆论生态的核心内涵(nèihán)、问题与破解(pòjiě)之道[J].青年记者,2022(18):20-23.
[26]张志安,吴涛(wútāo).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互联网治理[J].新疆师范大学(xīnjiāngshīfàndàxué)学报(xuébào)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15,36(5):73-77+2.
[27]虞鑫,兰旻.媒介治理:国家治理体系中(zhōng)的(de)媒介角色——反思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与政治(zhèngzhì)[J].当代传播,2020(06):34-38.
[29]张志安(zhāngzhìān),冉桢.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:路径、效果与特征[J].新闻(xīnwén)与写作,2022(05):57-69.
[30]蔡礼强(càilǐqiáng),张晓彤.党的领导与(yǔ)国家治理现代化:功能定位与实现方式[J].中国行政管理(guǎnlǐ),2023,39(10):14-20.
[31]朱清河(qīnghé).中国共产党“党管媒体”的历史回溯与未来(wèilái)展望[J].青年记者,2021(12):14-17.
[32]陈昌凤,杨依军.意识形态安全(ānquán)与党管(dǎngguǎn)媒体原则:中国媒体融合政策(zhèngcè)之形成与体系建构[J].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2015,37(11):26-33.
[33]方兴东,何可,钟祥铭,等.中国网络治理(zhìlǐ)30年:“一体多元(duōyuán)模式”的(de)演进历程与规律启示[J].传媒观察,2023(09):54-65.
[34]杨畅.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是政府公信力提升的(de)重要(zhòngyào)路径: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群众路线重要论述[J].湖南师范大学(húnánshīfàndàxué)社会科学学报,2022,51(6):26-31.
[35]邓岩(dèngyán).“互联网(hùliánwǎng)+群众路线”的内涵与践行进路:以社会资本为(wèi)分析视角[J].社会主义研究,2023(05):132-140.
[36]翟梦杰.大舆论场视域下网络新闻(wǎngluòxīnwén)评论(pínglùn)如何引导舆论[J].青年记者,2023(21):73-75.
[37]王仕勇.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(xīnwén)政策的创新发展:逻辑理路(lǐlù)、实践路径和基本特征(jīběntèzhēng)[J].新闻与传播研究,2024,31(9):19-31+126.
[38]任昌辉,巢乃鹏.我国(wǒguó)政府(zhèngfǔ)网络舆情综合治理创新路径研究:基于治理工具论(lùn)的分析视角[J].电子政务,2021(06):40-51.
[39]李小宇.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策略(cèlüè)结构(jiégòu)与演化研究[J].情报科学,2014,32(6):24-29.
[40]孙萍,刘瑞生.网络生态视角下社交(shèjiāo)媒体的内容管理(guǎnlǐ)探析(tànxī)[J].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2019,41(12):50-53.
[41]杨保军.当代(dāngdài)中国新闻学自主(zìzhǔ)知识体系的实践呈现方式[J].编辑之友,2024(08):5-13.
[42]景跃进.将(jiāng)政党带进来——国家与(yǔ)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[J].探索(tànsuǒ)与争鸣,2019(08):85-100+198.
[43]中共中央办公厅(zhōnggòngzhōngyāngbàngōngtīng)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(yìnfā)《“十四五”文化(wénhuà)发展(fāzhǎn)规划(guīhuà)》[EB/OL].(2022-08-16)[2025-01-28].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2022-08/16/content_5705612.htm.
[44]朱鸿军,王涛.全党办媒体: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(xiàquán)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(de)适配理论(lǐlùn)探索[J].新闻大学,2024(08):43-54+119.
陶天野,虞鑫.推进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和网络舆论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:政策定位、概念内涵(nèihán)和实践路径[J].青年记者,2025(04):13-20.
作者:陶天野(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(shuòshì)研究生);虞鑫(yúxīn)[(通讯作者)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深圳大学全球(quánqiú)传播研究院研究员]
来源(láiyuán):《青年记者》2025年第4期
 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“一体化管理”进行(jìnxíng)定位,随后对其(qí)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。
进入新时代以来,信息技术迅猛发展,重塑媒体形态、舆论生态(shēngtài)、文化业态。面对(duì)技术变革和国家现代化建设(jiànshè)的时代要求,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,提出“深化网络(wǎngluò)(wǎngluò)管理体制改革,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,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的改革要求,作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[1]。如何理解“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”(以下简称“一体化管理”)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?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(jìnniánlái)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“一体化管理”进行定位(dìngwèi),随后对其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(fēnxī)。
《决定》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,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(zhòngdà)任务,包括(bāokuò)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,优化文化服务和(hé)文化产品供给机制,健全网络(wǎngluò)综合治理体系(tǐxì)(tǐxì),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。在这一政策语境下提出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举措,完成了从战略目标到实践路径的深层次推进。
从直接文本来看,“一体化管理”首先是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(tǐxì)的(de)(de)重要一环。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从“对互联网实行科学管理”的要求发展(fāzhǎn)而来,秉承“建设网络强国”的使命,强调多(duō)(duō)维度、多主体、多目标、多手段的治理过程,反映了中国互联网治理理念(lǐniàn)的进化[2]。“一体化管理”以整体性思维促进多主体协同,助力互联网治理的系统性谋划、综合性治理、体系化推进。习近平总书记(zǒngshūjì)主持召开中央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提出,要逐步建立起涵盖(hángài)领导管理、正(zhèng)能量(néngliàng)传播、内容管控、社会协同、网络法治(fǎzhì)、技术治网等各方面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。其中(qízhōng),正能量传播和内容管控已经传达了一体两面的内涵:“正能量传播的实质是正能量内容的生产,而内容管控则是针对违法与不良信息的管制”,二者相互结合交叉和补充,成为当前网络综合治理经验的初步凝练[3]。在此基础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强调整合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,在党和国家整体统筹之下协同推进正向引导与反向(fǎnxiàng)监管,意在明确综合治网职责边界,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、属地管理和主管(zhǔguǎn)主办责任,既从内容生产端发力创新宣传形式,也(yě)从传播管理端发力把控舆论全程,最终实现网络空间的全局优化,确保主流价值观在线上线下的统一传播和有效覆盖[4]。
从时间维度(wéidù)来看,“一体化管理”与加快建设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的(de)(de)任务相辅相成。全媒体传播体系是(shì)(shì)媒体融合在舆论(yúlùn)引导中的重要运用模式[5],党的政策文件多次强调,对于媒体融合,“正能量是总要求,管得住是硬道理,用得好是真本事”,“一个标准,一体管理”是让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重要保证,也(yě)是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提升正面宣传质量的必要手段。一方面,作为(zuòwéi)(wèi)一个多元主体共在的复合型生态系统,全媒体传播体系最重要的特征是“主体的集合性”,不同性质(xìngzhì)、类型的主体具有不同的立场(lìchǎng)、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[6],因而(yīnér)需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,配套落实政策措施,为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[7]。这与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内在逻辑(luójí)是一致的,“一体化管理”在深化(shēnhuà)网络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,也对新闻宣传工作机制提出要求,从而(cóngér)能够结合信息化发展成果助力传媒管理创新。另一方面,内容建设是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核心任务,而网络舆论是传播效果的重要评估依据(yījù),能够反映社会主要矛盾,为解决“好新闻如何传播”的问题提供认知资源,“一体化管理”有利于从思维和认知模式层面深化媒体融合,塑造更深入、更具说服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,为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提供支持。
从宏观格局来看,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最终服务于(yú)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。在2023年全国(quánguó)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,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,事关国家长治久安,事关民族凝聚力和(hé)向心力,是一项(yīxiàng)极端重要的工作”[8],并提出“七个着力”作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和行动指南。其中,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、着力建设(jiànshè)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着力提升新闻(xīnwén)舆论(yúlùn)传播(chuánbō)(chuánbō)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三点,分别是开展(kāizhǎn)新闻宣传文化工作的根本保证、总体方向(fāngxiàng)和实践路径[9],“一体化管理”承接和贯通这三方面要求,立足实践实际,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行动指示。具体而言,随着(suízhe)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、主战场(zhǔzhànchǎng),网络空间(wǎngluòkōngjiān)的舆论传播便成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。网络舆论传播可以分为“讲什么”和“如何(rúhé)讲”两个方面,前者要求通过网络综合治理来把握舆论方向,后者要求通过全媒体传播创新舆论方式[10],“一体化管理”以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坚持(jiānchí),统筹把握网络舆论传播的方向和方式,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中,通过网络空间综合治理,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,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提供助力。
整体(zhěngtǐ)来看,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新举措,“一体化管理”体现了(le)守正创新的思想方法,承接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使命,助力(zhùlì)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建立健全,为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,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文化条件。
解析概念内涵及生成原理,是社会科学研究的(de)(de)基本前提。在讨论如何推进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之前,应当结合对应的历史和现实语境,梳理“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”、“网络舆论(yúlùn)”、“一体化”这些次级概念的内涵和逻辑关系,解析“一体化管理”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来源,即回答“是什么”“为什么”的问题。
首先(shǒuxiān)考察“一体化管理”作为一项实践的(de)(de)指向对象——“新闻宣传”和“网络舆论”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关系。在“宣传”“新闻宣传”“舆论”“新闻舆论”等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各种话语表达中,这两个概念为何(wèihé)被专门提出,又为何能够并举、合为一体?通过话语分析方法,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常用话语进行历时性考察,可以理解其(qí)背后的观念发展变化(biànhuà)过程,透视“一体化管理”的理论内核。
在(zài)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和近代史发展历程双重影响下,中国新闻传播很长时间以来整体偏重“宣传”[11],中国共产党(zhōngguógòngchǎndǎng)的新闻宣传观念也首先建立在传统鼓动宣传的基础上,从而能(néng)促进共产主义(gòngchǎnzhǔyì)思想传播,推动党组织发展壮大(fāzhǎnzhuàngdà)[12]。从语言学角度看,“宣传”自建党以来便是最常出现的政策词汇,而“新闻工作(gōngzuò)”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开始作为(zuòwéi)一个独立语汇出现在重要文件中;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党的“新闻”和“宣传”工作始终紧密联系,不过更多(duō)的是一种工作理念而非语用(yǔyòng)概念,直到20世纪末,江泽民、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新闻宣传工作发表了(le)一系列讲话,“新闻宣传”概念才开始逐渐盛行,成为官方的统一称呼[13]。
改革开放后,理论界逐渐开始从“舆论(yúlùn)”视角(shìjiǎo)认识新闻宣传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,并(bìng)通过专门化、自觉(zìjué)化的(de)(de)(de)(de)理论和思想建构,来“协同新闻宣传与舆论监督这两种不同特性的信息传播形态”[14]。江泽民(jiāngzémín)同志在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中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“舆论导向”概念(gàiniàn),此后(cǐhòu)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”成为以(yǐ)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新闻思想;在此基础上,2002年起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“舆论引导”作为核心概念来强调,在舆论方向正确性的基础上,进一步提出对舆论工作的“水平”与“能力”的重视[15]。与此同时,随着21世纪社会转型带来多元社会思潮,互联网(hùliánwǎng)平台兴起成为社会言论的新容器(róngqì)和放大器,“网络舆论”“网上舆论”有关(yǒuguān)的生态学现象和对应概念逐步(zhúbù)进入政策制定者视野。2013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“8·19”讲话中指出,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,“舆论引导工作”逐步被单列出来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。2016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“新闻舆论”这一概念,指出新闻舆论工作的各个方面、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。过去常用的“新闻宣传工作”变成了“新闻舆论工作”,体现(tǐxiàn)出党对互联网时代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。这次会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转型的标志性里程碑。
综观这一过程可以发现,随着话语使用的变化,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不断成熟和发展,具体体现为对新闻规律(guīlǜ)不断探索、对舆论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越发重视。从“宣传”到“新闻宣传”的发展,是让新闻观念回归本位,承认新闻传播(chuánbō)活动有其规律,自觉适应和运用规律做工作;“舆论引导”和“网上舆论”等概念的出现,说明党对受众自身主体性的认识和尊重(zūnzhòng)。从“宣传”到“舆论”的话语变化实现了从单向传播到多向互动的理念进化,反映出“自下而上的意见(yìjiàn)流动(liúdòng)视角”,表明党的新闻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与时俱进的先进特征(tèzhēng)。
在这一背景下,“推进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与网络舆论(yúlùn)一体化管理”将“新闻宣传”和“网络舆论”两个概念并(bìng)置,首先顺应了(le)党的(de)(de)新闻宣传舆论话语的历史演变(yǎnbiàn)趋势,对新闻、宣传、舆论三者之间(zhījiān)的关系重新进行了科学认识和定位,是当前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立场和方法的直接反映。进一步地,前述(qiánshù)种种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(guānniàn)(guānniàn)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解释了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底层逻辑。杨保军认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(héxīn)观念有四个:党性原则(dǎngxìngyuánzé)(dǎngxìngyuánzé)观念、人民中心观念、新闻规律观念、正确舆论观念[16]。不难发现,尽管后两者与前两者之间存在概念层次上的差别,但四者本质上是统一的:“新闻规律观念”是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的必然要求,“正确舆论观念”是重要的方法论观念,二者通过指导具体实践把“党性原则观念”和“人民中心观念”落到实处;“党性原则观念”和“人民中心观念”经由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的理论论证而不可分割,在党性原则的统领下,新闻的人民性与党领导(lǐngdǎo)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(xíngchéng)互构关系,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社会意志的凝聚和统合,从而(cóngér)对“为了谁,依靠谁,我是谁”这个根本问题作出回应[17]。建立在上述这些观念内涵基础上、以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为内核(nèihé)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也就由此具备了深入推进互联网时代公意形成的可能性,这使得它与党的宣传思想保持内在一致并在逻辑上一脉相承,从而能够获得(huòdé)理论上的合法性。
如前所述,将网络舆论(yúlùn)①纳入考量是新时代党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(de)必然要求,体现了(le)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的基本立场,保证了“一体化管理(guǎnlǐ)”在理论层面(céngmiàn)的合法性。下面,通过考察网络舆论的发展历程和特点,可以(kěyǐ)进一步明确“一体化管理”提出的现实语境,理解其中包含的问题意识。换言之,当前网络舆论生态呈现出何种特征和影响,使得“一体化管理”成为深化改革的必要手段?
按照媒介(méijiè)技术(jìshù)演进过程,网络舆论发展历程可以被分为“00”年代(niándài)(niándài)、“10”年代和“20”年代三个阶段,经历了从“网络舆论”到“网络舆论生态”的认知变化(huà),与“媒介化社会”的建构(jiàngòu)过程呈现出相似的逻辑。不同的传播技术下舆论生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,也对舆论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,已有不少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,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。
第一,主流媒体不再是传统模式下强有力(qiángyǒulì)的传播主体,融合转型成为长期任务。这一趋势在(zài)(zài)21世纪初就已出现(chūxiàn),随着互联网(hùliánwǎng)进入Web2.0阶段,以网络为依托由普通民众生成和传播的“民间(mínjiān)舆论场(chǎng)”由弱到强,越来越显性化(xiǎnxìnghuà),开始对媒体议程产生影响。在早期“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”和“陕西华南虎造假事件”等社会事件中,都是网民先自发形成大范围讨论,随后引来国内传统媒体报道(méitǐbàodào)和有关部门调查介入[18]。2011年起,微博、微信(wēixìn)和客户端构成的“两微一端”新媒体传播矩阵成为网络舆论的主要载体,赋予公众“传受合一(héyī)”的身份(shēnfèn),这种与传统模式截然相反的议题生成次序越发常见。一项实证研究表明,传统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机制正在被颠覆,技术赋权之下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舆论热点往往先于媒体报道,能够(nénggòu)推动媒体关注并调整议题,舆论监督形式也逐渐(zhújiàn)从媒体监督转为全民监督[19]。对此,主流媒体倘若无法及时调整自身定位和传播模式,便很容易在“事件增多、议题拓展(tuòzhǎn)、传播主体多样”三重压力下陷入被动状态,甚至落入“塔西佗陷阱”[20]。
第二,网络舆论生态越发复杂,治理(zhìlǐ)手段亟须升级。虽然社交媒体上(shàng)公众(gōngzhòng)舆论的(de)(de)生成过程拓展了公众表达(biǎodá)权的实现途径,但表达便利与“海量意见”并不(bù)等同于舆论的发达[21]。按网络舆论的存在(cúnzài)形态来看,互联网(hùliánwǎng)(hùliánwǎng)空间的潜舆论显化、显舆论复杂化、行为舆论虚拟化(xūnǐhuà),构成“众声喧哗”的舆论环境,情绪因素在其中的影响越发突出,原本现实社会中以“清晰(qīngxī)的公开(gōngkāi)意见”为主要形态的舆论难以形成(xíngchéng)气候,反而导致谣言认同(rèntóng)、网络犬儒主义和民粹式政治等“信任异化”现象[22][23];按网络舆论的传播规则来看,互联网“去中心化”的背后往往是自由市场权力规则下的“再中心化”,简单来说即谁拥有的信息(xìnxī)最多、谁的信息更能吸引注意,谁便拥有话语权和主导议程的能力[24]。到2020年前后,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,以算法、算力和数据为核心要素的“机器”作为新的行动者参与到多重社交终端和场景的传播中,“技术—平台—政府”三者的博弈更加激烈,数据驱动的“复合型(fùhéxíng)舆论场”渐成气候,网络舆论集成了政府、企业、公众乃至技术、算法等多主体意见,导致“流动性过剩”,越发呈现出分散化、圈层化倾向,打破舆论生态的动态平衡[25]。
这两方面问题对应着我国新时代新闻舆论(yúlùn)工作的(de)(de)两个面向:一是从舆论引导(yǐndǎo)的视角出发,对主流媒体的环境适应力、民意反映力、舆论引导力提出要求(yāoqiú),加快推进媒体融合转型;二是从舆论治理的视角出发,观照(guānzhào)互联网场(chǎng)域内不同主体(zhǔtǐ)的话语表达、传播逻辑、互动关系,探索互联网治理有效模式。二者(èrzhě)相辅相成,本质上是统一的。随着技术发展,这两方面工作势必要求进一步贯通和融合,通过体制机制的全方位(quánfāngwèi)改革,实现构建网上网下一体(yītǐ)、内宣外宣(wàixuān)联动的主流舆论新格局的根本任务。“一体化管理”由此承接了“主流舆论场”构建和“复合型舆论场”治理的双重要求,内在地包含了正面宣传、舆论监督(yúlùnjiāndū)、舆论引导、网络空间净化等多方面行动内容,成为实现两个面向统一性的具体手段。此时“一体”指的是方法论上的一致性,即无论是哪(nǎ)方面的工作内容,都需要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确保执行层面多主体、多手段的协调性,体现了治理思维的综合意义,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党委领导、政府管理、企业履责、社会(shèhuì)监督、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”的综合治网格局两相呼应。
中国互联网治理(zhìlǐ)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相当的(de)同构性,正由政府主导的传统管理形式转向政府、市场(shìchǎng)、社会(shèhuì)多元主体等共同参与的形式[26]。在此背景下提出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当然也需适应这一发展态势。习近平总书记对综合治网格局的论述(lùnshù)已经指出了“一体”的总要求和“多元”趋势之间的整体关系,但二者在实践层面的协同性具体(jùtǐ)为何、如何能实现,尚需要进一步考察。
随着网络社会崛起,“媒介逻辑”超越“事实逻辑”成为(chéngwéi)社会运行的(de)(de)主导性力量,往往要求重构国家、社会、市场等的角色和关系,建立一种多元(duōyuán)主体共同参与和协作的模式,以对这种力量进行约束(yuēshù)。然而,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逻辑的方案中(zhōng),有关“多主体共治”的尝试总潜在地包含了“去国家化”的理论立场[27],并在现实中带来令人失望的结果:当“多主体”上升为某种“主义”,它非但无法解决媒介化政治的根本问题,还导致了全球性的“互联网分裂”(Splinternet)和网络治理的“民主赤字”[28],严重危害了新闻业(xīnwényè)的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。此时(cǐshí),重新引入政府(zhèngfǔ)的力量、将治理权力收归民族国家,反而又成为全球性的趋势[29]。
与此不同的(de)是,在中(zhōng)国互联网治理(zhìlǐ)历程(lìchéng)中,国家(guójiā)(guójiā)始终处于核心(héxīn)主导地位。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(lǐngdǎo)下的制度体系,党的领导贯穿治党与治国的全过程,通过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,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[30]。因而在推进网络治理现代化(xiàndàihuà)的过程中,党对新闻宣传和(hé)网络空间的领导一以贯之,且随着新媒体环境的发展(fāzhǎn)变化而不断加强。具体可以从“党管媒体”和“党管网络”的行动路径中理解这一点:“党管媒体”是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核心原则(yuánzé),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“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”,要求通过政策引导(yǐndǎo)和技术规制(guīzhì)确保正确舆论导向。党管媒体,不能说只管党办(bàn)的媒体,而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,这个领导不是“隔靴搔痒式”领导,而是全局性、根本性的领导,方式可以有区别,但不能让党管媒体的原则被架空;“无论时代如何(rúhé)发展、媒体格局如何变化,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”[31]。随着技术发展,这一管理思路逐步拓展到更广泛的互联网空间。2013年,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,提出推动传统媒体(chuántǒngméitǐ)和新兴(xīnxīng)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,同时指出(zhǐchū)要“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”、“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”,将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紧紧关联(guānlián)在一起[32]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党和政府陆续出台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(guīdìng)》、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等作为规制手段,重视、发展和治理信息技术(xìnxījìshù)成为新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。2018年,国务院下发《国务院关于机构(jīgòu)设置的通知(tōngzhī)》,指出国家网信(wǎngxìn)办与中央网信办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,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,从而理顺网信办和国新办的职能分工,使前者专注于网络内容监管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治理,后者侧重对外宣传和国际舆论引导,进一步确保党对网络空间的领导效能。
不过,不论国家力量是(shì)“重新出场(chūchǎng)”还是“始终在场”,治理理念和措施都(dōu)需要随着环境变化而相应地更新,否则会陷入“只有底线思维,没有理论辩论;只讲(jiǎng)安全意识,不讲治理方略”的桎梏。换言之,对具体(jùtǐ)手段和方式的考虑,始终是党的领导下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应有之义,也是保证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统一性的前提。此时,党的功能定位(gōngnéngdìngwèi)是“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”:既总揽全局,又(yòu)不包揽一切,充分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。
因此,如果将中国特色的(de)网络(wǎngluò)治理(zhìlǐ)模式概括为“一体多元(duōyuán)模式”:党(dǎng)委和(hé)政府居于核心,其他主体居于外围、不同程度参与其中(qízhōng),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构筑(gòuzhù)的“同心圆”治理结构[33],那么“一体化管理”便是基于这一结构提出的创新措施,它在(zài)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构建“一体”和“多元”关系,实现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两方面工作的有效结合,这意味着在制度上从新闻管理和网络管理“两套班子”进一步(jìnyíbù)转向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全过程的“穿透式监管”,把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、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纳入管理范围,提高党和政府对“同心圆”内不同主体的统筹效能;在理念上明确中国互联网治理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为首要目的,从“党管媒体”、“党管网络”的分别行动模式,转变(zhuǎnbiàn)为“党管意识形态”理念下的整体性工作逻辑,使各(gè)部门、各领域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。
“一体化管理”的(de)合法性(héfǎxìng)、必要性、有效性,论证了其作为政策概念何以(héyǐ)可能,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(jìnyíbù)聚焦现实行动路径(lùjìng),考察它作为改革方向何以可为。《决定》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为“六个坚持(jiānchí)”:坚持党的全面领导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、坚持守正创新、坚持以制度建设(jiànshè)为主线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、坚持系统观念。这六项原则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布局提供了根本遵循,在此基础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实践方针和实现路径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。
第一,以服务党和人民(rénmín)(rénmín)(dǎnghérénmín)为根本,坚持网络群众路线(qúnzhònglùxiàn)。“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”是奠定“一体化管理”话语合法性(héfǎxìng)的(de)(de)(de)理论基础,服务党和人民是“一体化管理”的根本使命。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,而政治的核心在于(yú)权力,权力的核心在于民意,要确保“一体化管理”有效落实,必须尊重人民主体(zhǔtǐ)(zhǔtǐ)地位和首创精神,做到“人民有所呼、改革有所应”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领导干部(gànbù)要学网、懂网、用网,了解群众所思所愿,收集好想法好建议,积极回应网民关切”。互联网为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新的实践场域和技术支持,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成为政府公信力提升的重要途径,建立有效的政务网络平台,能够(nénggòu)快速收集社情民意并应用于科学决策,让网络舆论所反映出的社情民意成为凝聚共识的助推(zhùtuī)力;“互联网+群众路线”下党群关系(dǎngqúnguānxì)的“主体间性”特征,也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,为实现新闻媒体、平台企业、社会组织、用户个人等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模式夯实合作基石[34][35]。此外,新闻媒体也应把握平台、载体、导向等多方面的平衡,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,在“大舆论场”中发挥正向引导作用[36]。一个鲜活的例子是,2022年4月15日至5月16日,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,鼓励广大人民群众通过(tōngguò)人民日报社、新华社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提出意见建议。活动(huódòng)前后,主流媒体开展了全过程全方位的广泛宣传(xuānchuán),网民热烈讨论并积极建言献策(jiànyánxiàncè),各平台征求意见页面(yèmiàn)总阅读量达6.6亿次,收集各类留言超过854.2万条(wàntiáo),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注脚(zhùjiǎo)。
第二,以媒介技术变革为动能,推动管理制度创新(chuàngxīn)。《决定》指出:“坚持守正创新,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,紧跟时代步伐,顺应实践(shíjiàn)发展,突出问题导向,在新的(de)(de)起点上推进(tuījìn)理论创新、实践创新、制度创新、文化(wénhuà)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。”守正创新是党(dǎng)(dǎng)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,创新是大势所趋,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,也是“一体化管理”的核心要义,关于“怎样守正创新”的问题,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“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”,“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,该改(gǎi)的坚决改,不该改的不改”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为充分激发信息技术在新闻(xīnwén)传播领域的潜力,党和政府制定了媒介融合相关政策,推动党的新闻事业深度融入国家信息化(xìnxīhuà)建设(jiànshè)和社会治理(zhìlǐ)进程,以《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“互联网+”行动的指导意见》为代表的系列政策文件,旨在建立与新闻舆论工作(gōngzuò)相适应的规制框架(kuāngjià),激发传媒业(chuánméiyè)的核心竞争力[37]。对于“一体化管理”而言,技术驱动的制度创新同样是第一要务(yàowù),一方面,用科学化、制度化的网络舆情预防疏导机制代替“应激式”“运动式”管理传统,用“引领型、混合型”政府工具代替“强制型”工具,政府内部职能部门应结合具体情境厘清权责边界、达成理念共识,同时加快落实配套性(pèitàoxìng)的供给侧改革措施,支持外部主体(如媒体机构、企业(qǐyè)等)探索更有效的协同模式[38];另一方面,优化中国特色的“代理式”监管策略[39],利用超级平台企业提供的技术、数据和服务驱动国家数字化转型(zhuǎnxíng),建立人工智能驱动的舆情监测和分析(fēnxī)平台,实时追踪(zhuīzōng)新闻传播效果和网络舆情走势,分析了解(liǎojiě)受众需求和传播效果,通过新闻宣传的及时补位和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,避免舆论真空和失控。
第三(dìsān),以自主知识生产为引领,完善协同治理机制(jīzhì)。党的二十届三中(zhōng)全会《决定》提出,构建中国(zhōngguó)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,是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方面,而知识体系中的理论观念必须依据一定的中介手段转化为实践观念,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力量(lìliàng)和(hé)影响。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(guǎnlǐ)”立足“一体多元”网络治理模式的要求,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机制为实践目标,已有不少学者就不同社会主体(zhǔtǐ)的参与形式提出建议,如鼓励公众自主甄别信息、运用技术手段优化内容(nèiróng)过滤、建立平台间的合作机制等[40]。这些建议建立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上:随着媒介生态变革,以往的新闻专业知识常识化,职业新闻主体之外(zhīwài)的多种(duōzhǒng)社会主体成为新闻知识体系的运用者、呈现者,在新闻传播环境中承担不同的身份和角色。但想要确保各方面新闻生产活动(huódòng)能在“同心圆”结构中运转起来,更关键(guānjiàn)的是控制主体(即负责(fùzé)新闻领导和管理活动的主体)对新闻知识的理解和运用,并关系到不同主体间认知共识的建立[41]。这样一种认知成果实际上是对新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生产、知识体系构建提出要求,比如中国语境下的“协同治理”不同于(bùtóngyú)西方以博弈论、多中心治理等为基础的概念(gàiniàn),它提倡“党委领导,政府负责,社会协同”的党政一体化机制,这在根本上源于中国政党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在“国家与社会”这组关系中的角色[42],也与马克思主义(mǎkèsīzhǔyì)新闻观的底层逻辑(luójí)相契。以此为逻辑起点、以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大问题为导向开展(kāizhǎn)新闻学研究,才能构建有指导意义的知识结构,促进(cùjìn)科学的制度建设。
推进新闻宣传(xuānchuán)和网络舆论(yúlùn)一体化管理,是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(de)新要求(yāoqiú),为进一步(jìnyíbù)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抓手。党的“十四五”规划(guīhuà)指出,新闻传播既是事业又(yòu)是产业,既是阵地又是市场,既要宣传理论又要治理舆论,必须牢固树立系统观念,坚持统筹兼顾(tǒngchóujiāngù)、全面推进,才能促进系统集成、协同高效,实现文化发展质量、结构、规模(guīmó)、速度、效益、安全相统一[43]。在改革思路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以系统观念为核心(héxīn)指导,突出整体性、协同性、系统性,通过传统媒体领域和新兴媒体领域在管理机制上的深度融合,形成从内容生产到舆论治理的全链条、全流程管理模式,为应对网络舆论场复杂生态、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提供支持。
“一体化管理”是“党管媒体(méitǐ)”原则在(zài)当前外部环境变局下的(de)(de)(de)重要适应性举措。“党管媒体”是中(zhōng)国新闻媒体凝聚社会公意的前提,随着互联网成为宣传思想工作(gōngzuò)的主阵地,一方面,“党管媒体”的客体和主体范畴不断扩大,管理主体不局限于党和政府宣传部门,所指对象也不仅仅是由党直接(zhíjiē)掌握的媒体;另一方面,传统的新闻舆论(yúlùn)(yúlùn)主客体界限逐渐模糊,并在新媒体传播的动态过程中互相转化和融合,此时“一体”是具有综合性思维、囊括多元(duōyuán)主体的“一体”。如习近平总书记在“8·19”讲话中指出的,“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,动员(dòngyuán)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,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、行业管理、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”。应当发挥新闻宣传和网络(wǎngluò)舆论的协调合作优势,动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“办(管)”好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、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主体,实现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补充[44]。
技术革命日新月异,对于“一体化管理(guǎnlǐ)”要(yào)“管什么”、“怎么管”问题的回答始终需要更新(gēngxīn)和调整。在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要求的过程中,应当以党的领导为(wèi)根本原则,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、求真务实,不断探索新闻舆论工作新方法、新手段(shǒuduàn);学界也应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逻辑起点、以国家重大问题为导向(dǎoxiàng)、以本土经验为原材料,通过知识生产、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学术价值(jiàzhí),共同促进中国(zhōngguó)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完善,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更加健全,文化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。
【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“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坚守新闻真实性的路径、机制(jīzhì)与方法研究(yánjiū)”(批准(pīzhǔn)号:21CXW001)、深圳大学科研启动(qǐdòng)经费课题“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研究”成果】
①需要指出的是,如今学界(xuéjiè)在讨论“舆论”时,基本默认是指以互联网为表达渠道的“网络舆论”,但事实上(shàng)(shàng),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,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直到(zhídào)2015年底才超过50%,具备表达多数人意见的数量(shùliàng)基础;这些网络言论(yánlùn)内部也并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共识(所谓“公意”)以形成真正意义(yìyì)上的“舆论”,因此本文所说的“网络舆论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理性概念,而是以现象和问题为导向的广义概念。
[1]中共中央关于(guānyú)进一步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推进(tuījìn)中国式现代化的(de)决定[EB/OL].(2024-07-21)[2025-01-25].http://www.news.cn/politics/20240721/cec09ea2bde840dfb99331c48ab5523a/c.html.
[2]周净泓.构建(gòujiàn)安全平衡(pínghéng)发展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[J].青年记者,2021(04):105-106.
[3]郭全中,李黎.网络综合治理体系:概念沿革、生成逻辑(luójí)与实践路径(lùjìng)[J].传媒观察,2023(07):104-111.
[4]张居永.全媒体(méitǐ)时代网络舆论(yúlùn)生态治理策略研究[J].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,2021(09):81-84.
[5]叶俊(yèjùn).重塑舆论中心:媒体融合在舆论引导中的(de)运用与创新[J].新闻爱好者,2023(06):21-26.
[6]杨保军(yángbǎojūn),樊攀.多元主体协同: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升级的主导方向[J].传媒观察,2024(01):57-67.
[7]罗昕,张瑾杰.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基本内涵、评价(píngjià)标准与建设路径(lùjìng)[J].中国编辑,2023(10):30-36+53.
[8]习近平(xíjìnpíng)对宣传(xuānchuán)思想文化(wénhuà)工作(gōngzuò)作出重要指示[EB/OL].(2023-10-08)[2025-01-25]. http://www.news.cn/politics/leaders/2023-10/08/c_1129904890.htm.
[9]韩喜平,杨羽川.新(xīn)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指南(zhǐnán):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[J].思想理论教育(jiàoyù),2023(11):4-10.
[10]杨志超.全媒体时代推进网络意识形态(yìshíxíngtài)安全治理论(lǐlùn)析[J].思想战线,2024,50(3):112-119.
[11]梅(méi)琼林,郭万盛.中国新闻(xīnwén)传播对宣传之偏重(piānzhòng)的文化探源[J].上海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7(01):88-94.
[12]叶俊.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概念的历史及其(jíqí)终结[J].全球传媒学刊,2016,3(4):97-109.
[13]秦绍德.新闻舆论(yúlùn)工作(gōngzuò)核心概念刍论[J].新闻大学,2021(12):1-10+120.
[14]董天策,陈彦蓉,石钰婧.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舆论工作核心理念创新的百年进程:基于观念(guānniàn)史的视角(shìjiǎo)[J].当代传播(chuánbō),2021(06):4-11+24.
[15]樊亚平,刘静.舆论宣传·舆论导向·舆论引导(yǐndǎo):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[J].兰州大学(lánzhōudàxué)学报(社会科学版(bǎn)),2011,39(4):6-13.
[16]杨保军.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(mǎkèsīzhǔyì)新闻(xīnwén)观的核心观念(guānniàn)及其基本关系[J].新闻大学,2017(04):18-25+40+146.
[17]虞鑫,刘钊宁.从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到人民性:媒体的两种不同(bùtóng)公意形成之路[J].当代传播,2023(01):37-43.
[18]黄浩宇(huánghàoyǔ),方兴东,王奔.中国网络舆论30年:从(cóng)内容驱动走向数据驱动[J].传媒观察,2023(10):34-40.
[19]郭淼,杨济遥.倒置的传导:反向议程设置(shèzhì)视角下被(bèi)遮蔽的舆论(yúlùn)沟:以唐山打人事件为例[J].新闻界,2023(10):52-63.
[20]奉盛岚.“两个舆论(yúlùn)场”的溯源、发展(fāzhǎn)与当代意义探究[J].新闻研究导刊,2023,14(22):83-85.
[21]周葆华.社会化媒体(méitǐ)时代的舆论研究:概念、议题(yìtí)与创新[J].南京社会科学,2014(01):115-122.
[22]陈力丹,林羽丰(línyǔfēng).再论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[J].社会科学战线(zhànxiàn),2015(11):174-179.
[23] 全燕.“后真相时代”社交网络的(de)信任异化(yìhuà)现象研究[J].南京社会科学,2017(07):112-119.
[24]谢金林.网络舆论(yúlùn)生态系统内在机理(jīlǐ)及其治理研究——以网络政治舆论为分析视角[J].上海行政学院学报(xuébào),2013,14(4):90-101.
[25] 靖鸣,白龙.智媒时代网络舆论生态的核心内涵(nèihán)、问题与破解(pòjiě)之道[J].青年记者,2022(18):20-23.
[26]张志安,吴涛(wútāo).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互联网治理[J].新疆师范大学(xīnjiāngshīfàndàxué)学报(xuébào)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15,36(5):73-77+2.
[27]虞鑫,兰旻.媒介治理:国家治理体系中(zhōng)的(de)媒介角色——反思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与政治(zhèngzhì)[J].当代传播,2020(06):34-38.
[29]张志安(zhāngzhìān),冉桢.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:路径、效果与特征[J].新闻(xīnwén)与写作,2022(05):57-69.
[30]蔡礼强(càilǐqiáng),张晓彤.党的领导与(yǔ)国家治理现代化:功能定位与实现方式[J].中国行政管理(guǎnlǐ),2023,39(10):14-20.
[31]朱清河(qīnghé).中国共产党“党管媒体”的历史回溯与未来(wèilái)展望[J].青年记者,2021(12):14-17.
[32]陈昌凤,杨依军.意识形态安全(ānquán)与党管(dǎngguǎn)媒体原则:中国媒体融合政策(zhèngcè)之形成与体系建构[J].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2015,37(11):26-33.
[33]方兴东,何可,钟祥铭,等.中国网络治理(zhìlǐ)30年:“一体多元(duōyuán)模式”的(de)演进历程与规律启示[J].传媒观察,2023(09):54-65.
[34]杨畅.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是政府公信力提升的(de)重要(zhòngyào)路径: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群众路线重要论述[J].湖南师范大学(húnánshīfàndàxué)社会科学学报,2022,51(6):26-31.
[35]邓岩(dèngyán).“互联网(hùliánwǎng)+群众路线”的内涵与践行进路:以社会资本为(wèi)分析视角[J].社会主义研究,2023(05):132-140.
[36]翟梦杰.大舆论场视域下网络新闻(wǎngluòxīnwén)评论(pínglùn)如何引导舆论[J].青年记者,2023(21):73-75.
[37]王仕勇.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(xīnwén)政策的创新发展:逻辑理路(lǐlù)、实践路径和基本特征(jīběntèzhēng)[J].新闻与传播研究,2024,31(9):19-31+126.
[38]任昌辉,巢乃鹏.我国(wǒguó)政府(zhèngfǔ)网络舆情综合治理创新路径研究:基于治理工具论(lùn)的分析视角[J].电子政务,2021(06):40-51.
[39]李小宇.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策略(cèlüè)结构(jiégòu)与演化研究[J].情报科学,2014,32(6):24-29.
[40]孙萍,刘瑞生.网络生态视角下社交(shèjiāo)媒体的内容管理(guǎnlǐ)探析(tànxī)[J].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2019,41(12):50-53.
[41]杨保军.当代(dāngdài)中国新闻学自主(zìzhǔ)知识体系的实践呈现方式[J].编辑之友,2024(08):5-13.
[42]景跃进.将(jiāng)政党带进来——国家与(yǔ)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[J].探索(tànsuǒ)与争鸣,2019(08):85-100+198.
[43]中共中央办公厅(zhōnggòngzhōngyāngbàngōngtīng)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(yìnfā)《“十四五”文化(wénhuà)发展(fāzhǎn)规划(guīhuà)》[EB/OL].(2022-08-16)[2025-01-28].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2022-08/16/content_5705612.htm.
[44]朱鸿军,王涛.全党办媒体: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(xiàquán)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(de)适配理论(lǐlùn)探索[J].新闻大学,2024(08):43-54+119.
陶天野,虞鑫.推进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和网络舆论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:政策定位、概念内涵(nèihán)和实践路径[J].青年记者,2025(04):13-20.
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“一体化管理”进行(jìnxíng)定位,随后对其(qí)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。
进入新时代以来,信息技术迅猛发展,重塑媒体形态、舆论生态(shēngtài)、文化业态。面对(duì)技术变革和国家现代化建设(jiànshè)的时代要求,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,提出“深化网络(wǎngluò)(wǎngluò)管理体制改革,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,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的改革要求,作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[1]。如何理解“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”(以下简称“一体化管理”)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?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(jìnniánlái)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“一体化管理”进行定位(dìngwèi),随后对其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(fēnxī)。
《决定》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,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(zhòngdà)任务,包括(bāokuò)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,优化文化服务和(hé)文化产品供给机制,健全网络(wǎngluò)综合治理体系(tǐxì)(tǐxì),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。在这一政策语境下提出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举措,完成了从战略目标到实践路径的深层次推进。
从直接文本来看,“一体化管理”首先是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(tǐxì)的(de)(de)重要一环。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从“对互联网实行科学管理”的要求发展(fāzhǎn)而来,秉承“建设网络强国”的使命,强调多(duō)(duō)维度、多主体、多目标、多手段的治理过程,反映了中国互联网治理理念(lǐniàn)的进化[2]。“一体化管理”以整体性思维促进多主体协同,助力互联网治理的系统性谋划、综合性治理、体系化推进。习近平总书记(zǒngshūjì)主持召开中央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提出,要逐步建立起涵盖(hángài)领导管理、正(zhèng)能量(néngliàng)传播、内容管控、社会协同、网络法治(fǎzhì)、技术治网等各方面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。其中(qízhōng),正能量传播和内容管控已经传达了一体两面的内涵:“正能量传播的实质是正能量内容的生产,而内容管控则是针对违法与不良信息的管制”,二者相互结合交叉和补充,成为当前网络综合治理经验的初步凝练[3]。在此基础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强调整合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,在党和国家整体统筹之下协同推进正向引导与反向(fǎnxiàng)监管,意在明确综合治网职责边界,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、属地管理和主管(zhǔguǎn)主办责任,既从内容生产端发力创新宣传形式,也(yě)从传播管理端发力把控舆论全程,最终实现网络空间的全局优化,确保主流价值观在线上线下的统一传播和有效覆盖[4]。
从时间维度(wéidù)来看,“一体化管理”与加快建设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的(de)(de)任务相辅相成。全媒体传播体系是(shì)(shì)媒体融合在舆论(yúlùn)引导中的重要运用模式[5],党的政策文件多次强调,对于媒体融合,“正能量是总要求,管得住是硬道理,用得好是真本事”,“一个标准,一体管理”是让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重要保证,也(yě)是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提升正面宣传质量的必要手段。一方面,作为(zuòwéi)(wèi)一个多元主体共在的复合型生态系统,全媒体传播体系最重要的特征是“主体的集合性”,不同性质(xìngzhì)、类型的主体具有不同的立场(lìchǎng)、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[6],因而(yīnér)需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,配套落实政策措施,为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[7]。这与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内在逻辑(luójí)是一致的,“一体化管理”在深化(shēnhuà)网络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,也对新闻宣传工作机制提出要求,从而(cóngér)能够结合信息化发展成果助力传媒管理创新。另一方面,内容建设是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核心任务,而网络舆论是传播效果的重要评估依据(yījù),能够反映社会主要矛盾,为解决“好新闻如何传播”的问题提供认知资源,“一体化管理”有利于从思维和认知模式层面深化媒体融合,塑造更深入、更具说服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,为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提供支持。
从宏观格局来看,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最终服务于(yú)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。在2023年全国(quánguó)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,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,事关国家长治久安,事关民族凝聚力和(hé)向心力,是一项(yīxiàng)极端重要的工作”[8],并提出“七个着力”作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和行动指南。其中,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、着力建设(jiànshè)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着力提升新闻(xīnwén)舆论(yúlùn)传播(chuánbō)(chuánbō)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三点,分别是开展(kāizhǎn)新闻宣传文化工作的根本保证、总体方向(fāngxiàng)和实践路径[9],“一体化管理”承接和贯通这三方面要求,立足实践实际,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行动指示。具体而言,随着(suízhe)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、主战场(zhǔzhànchǎng),网络空间(wǎngluòkōngjiān)的舆论传播便成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。网络舆论传播可以分为“讲什么”和“如何(rúhé)讲”两个方面,前者要求通过网络综合治理来把握舆论方向,后者要求通过全媒体传播创新舆论方式[10],“一体化管理”以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坚持(jiānchí),统筹把握网络舆论传播的方向和方式,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中,通过网络空间综合治理,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,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提供助力。
整体(zhěngtǐ)来看,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新举措,“一体化管理”体现了(le)守正创新的思想方法,承接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使命,助力(zhùlì)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建立健全,为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,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文化条件。
解析概念内涵及生成原理,是社会科学研究的(de)(de)基本前提。在讨论如何推进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之前,应当结合对应的历史和现实语境,梳理“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”、“网络舆论(yúlùn)”、“一体化”这些次级概念的内涵和逻辑关系,解析“一体化管理”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来源,即回答“是什么”“为什么”的问题。
首先(shǒuxiān)考察“一体化管理”作为一项实践的(de)(de)指向对象——“新闻宣传”和“网络舆论”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关系。在“宣传”“新闻宣传”“舆论”“新闻舆论”等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各种话语表达中,这两个概念为何(wèihé)被专门提出,又为何能够并举、合为一体?通过话语分析方法,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常用话语进行历时性考察,可以理解其(qí)背后的观念发展变化(biànhuà)过程,透视“一体化管理”的理论内核。
在(zài)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和近代史发展历程双重影响下,中国新闻传播很长时间以来整体偏重“宣传”[11],中国共产党(zhōngguógòngchǎndǎng)的新闻宣传观念也首先建立在传统鼓动宣传的基础上,从而能(néng)促进共产主义(gòngchǎnzhǔyì)思想传播,推动党组织发展壮大(fāzhǎnzhuàngdà)[12]。从语言学角度看,“宣传”自建党以来便是最常出现的政策词汇,而“新闻工作(gōngzuò)”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开始作为(zuòwéi)一个独立语汇出现在重要文件中;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党的“新闻”和“宣传”工作始终紧密联系,不过更多(duō)的是一种工作理念而非语用(yǔyòng)概念,直到20世纪末,江泽民、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新闻宣传工作发表了(le)一系列讲话,“新闻宣传”概念才开始逐渐盛行,成为官方的统一称呼[13]。
改革开放后,理论界逐渐开始从“舆论(yúlùn)”视角(shìjiǎo)认识新闻宣传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,并(bìng)通过专门化、自觉(zìjué)化的(de)(de)(de)(de)理论和思想建构,来“协同新闻宣传与舆论监督这两种不同特性的信息传播形态”[14]。江泽民(jiāngzémín)同志在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中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“舆论导向”概念(gàiniàn),此后(cǐhòu)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”成为以(yǐ)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新闻思想;在此基础上,2002年起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“舆论引导”作为核心概念来强调,在舆论方向正确性的基础上,进一步提出对舆论工作的“水平”与“能力”的重视[15]。与此同时,随着21世纪社会转型带来多元社会思潮,互联网(hùliánwǎng)平台兴起成为社会言论的新容器(róngqì)和放大器,“网络舆论”“网上舆论”有关(yǒuguān)的生态学现象和对应概念逐步(zhúbù)进入政策制定者视野。2013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“8·19”讲话中指出,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,“舆论引导工作”逐步被单列出来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。2016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“新闻舆论”这一概念,指出新闻舆论工作的各个方面、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。过去常用的“新闻宣传工作”变成了“新闻舆论工作”,体现(tǐxiàn)出党对互联网时代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。这次会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转型的标志性里程碑。
综观这一过程可以发现,随着话语使用的变化,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不断成熟和发展,具体体现为对新闻规律(guīlǜ)不断探索、对舆论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越发重视。从“宣传”到“新闻宣传”的发展,是让新闻观念回归本位,承认新闻传播(chuánbō)活动有其规律,自觉适应和运用规律做工作;“舆论引导”和“网上舆论”等概念的出现,说明党对受众自身主体性的认识和尊重(zūnzhòng)。从“宣传”到“舆论”的话语变化实现了从单向传播到多向互动的理念进化,反映出“自下而上的意见(yìjiàn)流动(liúdòng)视角”,表明党的新闻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与时俱进的先进特征(tèzhēng)。
在这一背景下,“推进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与网络舆论(yúlùn)一体化管理”将“新闻宣传”和“网络舆论”两个概念并(bìng)置,首先顺应了(le)党的(de)(de)新闻宣传舆论话语的历史演变(yǎnbiàn)趋势,对新闻、宣传、舆论三者之间(zhījiān)的关系重新进行了科学认识和定位,是当前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立场和方法的直接反映。进一步地,前述(qiánshù)种种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(guānniàn)(guānniàn)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解释了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底层逻辑。杨保军认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(héxīn)观念有四个:党性原则(dǎngxìngyuánzé)(dǎngxìngyuánzé)观念、人民中心观念、新闻规律观念、正确舆论观念[16]。不难发现,尽管后两者与前两者之间存在概念层次上的差别,但四者本质上是统一的:“新闻规律观念”是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的必然要求,“正确舆论观念”是重要的方法论观念,二者通过指导具体实践把“党性原则观念”和“人民中心观念”落到实处;“党性原则观念”和“人民中心观念”经由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的理论论证而不可分割,在党性原则的统领下,新闻的人民性与党领导(lǐngdǎo)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(xíngchéng)互构关系,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社会意志的凝聚和统合,从而(cóngér)对“为了谁,依靠谁,我是谁”这个根本问题作出回应[17]。建立在上述这些观念内涵基础上、以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为内核(nèihé)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也就由此具备了深入推进互联网时代公意形成的可能性,这使得它与党的宣传思想保持内在一致并在逻辑上一脉相承,从而能够获得(huòdé)理论上的合法性。
如前所述,将网络舆论(yúlùn)①纳入考量是新时代党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(de)必然要求,体现了(le)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的基本立场,保证了“一体化管理(guǎnlǐ)”在理论层面(céngmiàn)的合法性。下面,通过考察网络舆论的发展历程和特点,可以(kěyǐ)进一步明确“一体化管理”提出的现实语境,理解其中包含的问题意识。换言之,当前网络舆论生态呈现出何种特征和影响,使得“一体化管理”成为深化改革的必要手段?
按照媒介(méijiè)技术(jìshù)演进过程,网络舆论发展历程可以被分为“00”年代(niándài)(niándài)、“10”年代和“20”年代三个阶段,经历了从“网络舆论”到“网络舆论生态”的认知变化(huà),与“媒介化社会”的建构(jiàngòu)过程呈现出相似的逻辑。不同的传播技术下舆论生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,也对舆论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,已有不少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,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。
第一,主流媒体不再是传统模式下强有力(qiángyǒulì)的传播主体,融合转型成为长期任务。这一趋势在(zài)(zài)21世纪初就已出现(chūxiàn),随着互联网(hùliánwǎng)进入Web2.0阶段,以网络为依托由普通民众生成和传播的“民间(mínjiān)舆论场(chǎng)”由弱到强,越来越显性化(xiǎnxìnghuà),开始对媒体议程产生影响。在早期“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”和“陕西华南虎造假事件”等社会事件中,都是网民先自发形成大范围讨论,随后引来国内传统媒体报道(méitǐbàodào)和有关部门调查介入[18]。2011年起,微博、微信(wēixìn)和客户端构成的“两微一端”新媒体传播矩阵成为网络舆论的主要载体,赋予公众“传受合一(héyī)”的身份(shēnfèn),这种与传统模式截然相反的议题生成次序越发常见。一项实证研究表明,传统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机制正在被颠覆,技术赋权之下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舆论热点往往先于媒体报道,能够(nénggòu)推动媒体关注并调整议题,舆论监督形式也逐渐(zhújiàn)从媒体监督转为全民监督[19]。对此,主流媒体倘若无法及时调整自身定位和传播模式,便很容易在“事件增多、议题拓展(tuòzhǎn)、传播主体多样”三重压力下陷入被动状态,甚至落入“塔西佗陷阱”[20]。
第二,网络舆论生态越发复杂,治理(zhìlǐ)手段亟须升级。虽然社交媒体上(shàng)公众(gōngzhòng)舆论的(de)(de)生成过程拓展了公众表达(biǎodá)权的实现途径,但表达便利与“海量意见”并不(bù)等同于舆论的发达[21]。按网络舆论的存在(cúnzài)形态来看,互联网(hùliánwǎng)(hùliánwǎng)空间的潜舆论显化、显舆论复杂化、行为舆论虚拟化(xūnǐhuà),构成“众声喧哗”的舆论环境,情绪因素在其中的影响越发突出,原本现实社会中以“清晰(qīngxī)的公开(gōngkāi)意见”为主要形态的舆论难以形成(xíngchéng)气候,反而导致谣言认同(rèntóng)、网络犬儒主义和民粹式政治等“信任异化”现象[22][23];按网络舆论的传播规则来看,互联网“去中心化”的背后往往是自由市场权力规则下的“再中心化”,简单来说即谁拥有的信息(xìnxī)最多、谁的信息更能吸引注意,谁便拥有话语权和主导议程的能力[24]。到2020年前后,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,以算法、算力和数据为核心要素的“机器”作为新的行动者参与到多重社交终端和场景的传播中,“技术—平台—政府”三者的博弈更加激烈,数据驱动的“复合型(fùhéxíng)舆论场”渐成气候,网络舆论集成了政府、企业、公众乃至技术、算法等多主体意见,导致“流动性过剩”,越发呈现出分散化、圈层化倾向,打破舆论生态的动态平衡[25]。
这两方面问题对应着我国新时代新闻舆论(yúlùn)工作的(de)(de)两个面向:一是从舆论引导(yǐndǎo)的视角出发,对主流媒体的环境适应力、民意反映力、舆论引导力提出要求(yāoqiú),加快推进媒体融合转型;二是从舆论治理的视角出发,观照(guānzhào)互联网场(chǎng)域内不同主体(zhǔtǐ)的话语表达、传播逻辑、互动关系,探索互联网治理有效模式。二者(èrzhě)相辅相成,本质上是统一的。随着技术发展,这两方面工作势必要求进一步贯通和融合,通过体制机制的全方位(quánfāngwèi)改革,实现构建网上网下一体(yītǐ)、内宣外宣(wàixuān)联动的主流舆论新格局的根本任务。“一体化管理”由此承接了“主流舆论场”构建和“复合型舆论场”治理的双重要求,内在地包含了正面宣传、舆论监督(yúlùnjiāndū)、舆论引导、网络空间净化等多方面行动内容,成为实现两个面向统一性的具体手段。此时“一体”指的是方法论上的一致性,即无论是哪(nǎ)方面的工作内容,都需要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确保执行层面多主体、多手段的协调性,体现了治理思维的综合意义,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党委领导、政府管理、企业履责、社会(shèhuì)监督、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”的综合治网格局两相呼应。
中国互联网治理(zhìlǐ)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相当的(de)同构性,正由政府主导的传统管理形式转向政府、市场(shìchǎng)、社会(shèhuì)多元主体等共同参与的形式[26]。在此背景下提出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当然也需适应这一发展态势。习近平总书记对综合治网格局的论述(lùnshù)已经指出了“一体”的总要求和“多元”趋势之间的整体关系,但二者在实践层面的协同性具体(jùtǐ)为何、如何能实现,尚需要进一步考察。
随着网络社会崛起,“媒介逻辑”超越“事实逻辑”成为(chéngwéi)社会运行的(de)(de)主导性力量,往往要求重构国家、社会、市场等的角色和关系,建立一种多元(duōyuán)主体共同参与和协作的模式,以对这种力量进行约束(yuēshù)。然而,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逻辑的方案中(zhōng),有关“多主体共治”的尝试总潜在地包含了“去国家化”的理论立场[27],并在现实中带来令人失望的结果:当“多主体”上升为某种“主义”,它非但无法解决媒介化政治的根本问题,还导致了全球性的“互联网分裂”(Splinternet)和网络治理的“民主赤字”[28],严重危害了新闻业(xīnwényè)的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。此时(cǐshí),重新引入政府(zhèngfǔ)的力量、将治理权力收归民族国家,反而又成为全球性的趋势[29]。
与此不同的(de)是,在中(zhōng)国互联网治理(zhìlǐ)历程(lìchéng)中,国家(guójiā)(guójiā)始终处于核心(héxīn)主导地位。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(lǐngdǎo)下的制度体系,党的领导贯穿治党与治国的全过程,通过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,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[30]。因而在推进网络治理现代化(xiàndàihuà)的过程中,党对新闻宣传和(hé)网络空间的领导一以贯之,且随着新媒体环境的发展(fāzhǎn)变化而不断加强。具体可以从“党管媒体”和“党管网络”的行动路径中理解这一点:“党管媒体”是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核心原则(yuánzé),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“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”,要求通过政策引导(yǐndǎo)和技术规制(guīzhì)确保正确舆论导向。党管媒体,不能说只管党办(bàn)的媒体,而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,这个领导不是“隔靴搔痒式”领导,而是全局性、根本性的领导,方式可以有区别,但不能让党管媒体的原则被架空;“无论时代如何(rúhé)发展、媒体格局如何变化,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”[31]。随着技术发展,这一管理思路逐步拓展到更广泛的互联网空间。2013年,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,提出推动传统媒体(chuántǒngméitǐ)和新兴(xīnxīng)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,同时指出(zhǐchū)要“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”、“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”,将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紧紧关联(guānlián)在一起[32]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党和政府陆续出台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(guīdìng)》、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等作为规制手段,重视、发展和治理信息技术(xìnxījìshù)成为新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。2018年,国务院下发《国务院关于机构(jīgòu)设置的通知(tōngzhī)》,指出国家网信(wǎngxìn)办与中央网信办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,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,从而理顺网信办和国新办的职能分工,使前者专注于网络内容监管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治理,后者侧重对外宣传和国际舆论引导,进一步确保党对网络空间的领导效能。
不过,不论国家力量是(shì)“重新出场(chūchǎng)”还是“始终在场”,治理理念和措施都(dōu)需要随着环境变化而相应地更新,否则会陷入“只有底线思维,没有理论辩论;只讲(jiǎng)安全意识,不讲治理方略”的桎梏。换言之,对具体(jùtǐ)手段和方式的考虑,始终是党的领导下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应有之义,也是保证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统一性的前提。此时,党的功能定位(gōngnéngdìngwèi)是“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”:既总揽全局,又(yòu)不包揽一切,充分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。
因此,如果将中国特色的(de)网络(wǎngluò)治理(zhìlǐ)模式概括为“一体多元(duōyuán)模式”:党(dǎng)委和(hé)政府居于核心,其他主体居于外围、不同程度参与其中(qízhōng),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构筑(gòuzhù)的“同心圆”治理结构[33],那么“一体化管理”便是基于这一结构提出的创新措施,它在(zài)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构建“一体”和“多元”关系,实现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两方面工作的有效结合,这意味着在制度上从新闻管理和网络管理“两套班子”进一步(jìnyíbù)转向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全过程的“穿透式监管”,把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、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纳入管理范围,提高党和政府对“同心圆”内不同主体的统筹效能;在理念上明确中国互联网治理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为首要目的,从“党管媒体”、“党管网络”的分别行动模式,转变(zhuǎnbiàn)为“党管意识形态”理念下的整体性工作逻辑,使各(gè)部门、各领域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。
“一体化管理”的(de)合法性(héfǎxìng)、必要性、有效性,论证了其作为政策概念何以(héyǐ)可能,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(jìnyíbù)聚焦现实行动路径(lùjìng),考察它作为改革方向何以可为。《决定》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为“六个坚持(jiānchí)”:坚持党的全面领导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、坚持守正创新、坚持以制度建设(jiànshè)为主线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、坚持系统观念。这六项原则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布局提供了根本遵循,在此基础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实践方针和实现路径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。
第一,以服务党和人民(rénmín)(rénmín)(dǎnghérénmín)为根本,坚持网络群众路线(qúnzhònglùxiàn)。“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”是奠定“一体化管理”话语合法性(héfǎxìng)的(de)(de)(de)理论基础,服务党和人民是“一体化管理”的根本使命。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,而政治的核心在于(yú)权力,权力的核心在于民意,要确保“一体化管理”有效落实,必须尊重人民主体(zhǔtǐ)(zhǔtǐ)地位和首创精神,做到“人民有所呼、改革有所应”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领导干部(gànbù)要学网、懂网、用网,了解群众所思所愿,收集好想法好建议,积极回应网民关切”。互联网为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新的实践场域和技术支持,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成为政府公信力提升的重要途径,建立有效的政务网络平台,能够(nénggòu)快速收集社情民意并应用于科学决策,让网络舆论所反映出的社情民意成为凝聚共识的助推(zhùtuī)力;“互联网+群众路线”下党群关系(dǎngqúnguānxì)的“主体间性”特征,也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,为实现新闻媒体、平台企业、社会组织、用户个人等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模式夯实合作基石[34][35]。此外,新闻媒体也应把握平台、载体、导向等多方面的平衡,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,在“大舆论场”中发挥正向引导作用[36]。一个鲜活的例子是,2022年4月15日至5月16日,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,鼓励广大人民群众通过(tōngguò)人民日报社、新华社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提出意见建议。活动(huódòng)前后,主流媒体开展了全过程全方位的广泛宣传(xuānchuán),网民热烈讨论并积极建言献策(jiànyánxiàncè),各平台征求意见页面(yèmiàn)总阅读量达6.6亿次,收集各类留言超过854.2万条(wàntiáo),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注脚(zhùjiǎo)。
第二,以媒介技术变革为动能,推动管理制度创新(chuàngxīn)。《决定》指出:“坚持守正创新,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,紧跟时代步伐,顺应实践(shíjiàn)发展,突出问题导向,在新的(de)(de)起点上推进(tuījìn)理论创新、实践创新、制度创新、文化(wénhuà)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。”守正创新是党(dǎng)(dǎng)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,创新是大势所趋,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,也是“一体化管理”的核心要义,关于“怎样守正创新”的问题,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“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”,“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,该改(gǎi)的坚决改,不该改的不改”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为充分激发信息技术在新闻(xīnwén)传播领域的潜力,党和政府制定了媒介融合相关政策,推动党的新闻事业深度融入国家信息化(xìnxīhuà)建设(jiànshè)和社会治理(zhìlǐ)进程,以《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“互联网+”行动的指导意见》为代表的系列政策文件,旨在建立与新闻舆论工作(gōngzuò)相适应的规制框架(kuāngjià),激发传媒业(chuánméiyè)的核心竞争力[37]。对于“一体化管理”而言,技术驱动的制度创新同样是第一要务(yàowù),一方面,用科学化、制度化的网络舆情预防疏导机制代替“应激式”“运动式”管理传统,用“引领型、混合型”政府工具代替“强制型”工具,政府内部职能部门应结合具体情境厘清权责边界、达成理念共识,同时加快落实配套性(pèitàoxìng)的供给侧改革措施,支持外部主体(如媒体机构、企业(qǐyè)等)探索更有效的协同模式[38];另一方面,优化中国特色的“代理式”监管策略[39],利用超级平台企业提供的技术、数据和服务驱动国家数字化转型(zhuǎnxíng),建立人工智能驱动的舆情监测和分析(fēnxī)平台,实时追踪(zhuīzōng)新闻传播效果和网络舆情走势,分析了解(liǎojiě)受众需求和传播效果,通过新闻宣传的及时补位和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,避免舆论真空和失控。
第三(dìsān),以自主知识生产为引领,完善协同治理机制(jīzhì)。党的二十届三中(zhōng)全会《决定》提出,构建中国(zhōngguó)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,是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方面,而知识体系中的理论观念必须依据一定的中介手段转化为实践观念,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力量(lìliàng)和(hé)影响。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(guǎnlǐ)”立足“一体多元”网络治理模式的要求,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机制为实践目标,已有不少学者就不同社会主体(zhǔtǐ)的参与形式提出建议,如鼓励公众自主甄别信息、运用技术手段优化内容(nèiróng)过滤、建立平台间的合作机制等[40]。这些建议建立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上:随着媒介生态变革,以往的新闻专业知识常识化,职业新闻主体之外(zhīwài)的多种(duōzhǒng)社会主体成为新闻知识体系的运用者、呈现者,在新闻传播环境中承担不同的身份和角色。但想要确保各方面新闻生产活动(huódòng)能在“同心圆”结构中运转起来,更关键(guānjiàn)的是控制主体(即负责(fùzé)新闻领导和管理活动的主体)对新闻知识的理解和运用,并关系到不同主体间认知共识的建立[41]。这样一种认知成果实际上是对新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生产、知识体系构建提出要求,比如中国语境下的“协同治理”不同于(bùtóngyú)西方以博弈论、多中心治理等为基础的概念(gàiniàn),它提倡“党委领导,政府负责,社会协同”的党政一体化机制,这在根本上源于中国政党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在“国家与社会”这组关系中的角色[42],也与马克思主义(mǎkèsīzhǔyì)新闻观的底层逻辑(luójí)相契。以此为逻辑起点、以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大问题为导向开展(kāizhǎn)新闻学研究,才能构建有指导意义的知识结构,促进(cùjìn)科学的制度建设。
推进新闻宣传(xuānchuán)和网络舆论(yúlùn)一体化管理,是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(de)新要求(yāoqiú),为进一步(jìnyíbù)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抓手。党的“十四五”规划(guīhuà)指出,新闻传播既是事业又(yòu)是产业,既是阵地又是市场,既要宣传理论又要治理舆论,必须牢固树立系统观念,坚持统筹兼顾(tǒngchóujiāngù)、全面推进,才能促进系统集成、协同高效,实现文化发展质量、结构、规模(guīmó)、速度、效益、安全相统一[43]。在改革思路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以系统观念为核心(héxīn)指导,突出整体性、协同性、系统性,通过传统媒体领域和新兴媒体领域在管理机制上的深度融合,形成从内容生产到舆论治理的全链条、全流程管理模式,为应对网络舆论场复杂生态、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提供支持。
“一体化管理”是“党管媒体(méitǐ)”原则在(zài)当前外部环境变局下的(de)(de)(de)重要适应性举措。“党管媒体”是中(zhōng)国新闻媒体凝聚社会公意的前提,随着互联网成为宣传思想工作(gōngzuò)的主阵地,一方面,“党管媒体”的客体和主体范畴不断扩大,管理主体不局限于党和政府宣传部门,所指对象也不仅仅是由党直接(zhíjiē)掌握的媒体;另一方面,传统的新闻舆论(yúlùn)(yúlùn)主客体界限逐渐模糊,并在新媒体传播的动态过程中互相转化和融合,此时“一体”是具有综合性思维、囊括多元(duōyuán)主体的“一体”。如习近平总书记在“8·19”讲话中指出的,“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,动员(dòngyuán)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,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、行业管理、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”。应当发挥新闻宣传和网络(wǎngluò)舆论的协调合作优势,动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“办(管)”好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、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主体,实现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补充[44]。
技术革命日新月异,对于“一体化管理(guǎnlǐ)”要(yào)“管什么”、“怎么管”问题的回答始终需要更新(gēngxīn)和调整。在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要求的过程中,应当以党的领导为(wèi)根本原则,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、求真务实,不断探索新闻舆论工作新方法、新手段(shǒuduàn);学界也应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逻辑起点、以国家重大问题为导向(dǎoxiàng)、以本土经验为原材料,通过知识生产、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学术价值(jiàzhí),共同促进中国(zhōngguó)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完善,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更加健全,文化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。
【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“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坚守新闻真实性的路径、机制(jīzhì)与方法研究(yánjiū)”(批准(pīzhǔn)号:21CXW001)、深圳大学科研启动(qǐdòng)经费课题“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研究”成果】
①需要指出的是,如今学界(xuéjiè)在讨论“舆论”时,基本默认是指以互联网为表达渠道的“网络舆论”,但事实上(shàng)(shàng),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,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直到(zhídào)2015年底才超过50%,具备表达多数人意见的数量(shùliàng)基础;这些网络言论(yánlùn)内部也并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共识(所谓“公意”)以形成真正意义(yìyì)上的“舆论”,因此本文所说的“网络舆论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理性概念,而是以现象和问题为导向的广义概念。
[1]中共中央关于(guānyú)进一步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推进(tuījìn)中国式现代化的(de)决定[EB/OL].(2024-07-21)[2025-01-25].http://www.news.cn/politics/20240721/cec09ea2bde840dfb99331c48ab5523a/c.html.
[2]周净泓.构建(gòujiàn)安全平衡(pínghéng)发展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[J].青年记者,2021(04):105-106.
[3]郭全中,李黎.网络综合治理体系:概念沿革、生成逻辑(luójí)与实践路径(lùjìng)[J].传媒观察,2023(07):104-111.
[4]张居永.全媒体(méitǐ)时代网络舆论(yúlùn)生态治理策略研究[J].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,2021(09):81-84.
[5]叶俊(yèjùn).重塑舆论中心:媒体融合在舆论引导中的(de)运用与创新[J].新闻爱好者,2023(06):21-26.
[6]杨保军(yángbǎojūn),樊攀.多元主体协同: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升级的主导方向[J].传媒观察,2024(01):57-67.
[7]罗昕,张瑾杰.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基本内涵、评价(píngjià)标准与建设路径(lùjìng)[J].中国编辑,2023(10):30-36+53.
[8]习近平(xíjìnpíng)对宣传(xuānchuán)思想文化(wénhuà)工作(gōngzuò)作出重要指示[EB/OL].(2023-10-08)[2025-01-25]. http://www.news.cn/politics/leaders/2023-10/08/c_1129904890.htm.
[9]韩喜平,杨羽川.新(xīn)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指南(zhǐnán):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[J].思想理论教育(jiàoyù),2023(11):4-10.
[10]杨志超.全媒体时代推进网络意识形态(yìshíxíngtài)安全治理论(lǐlùn)析[J].思想战线,2024,50(3):112-119.
[11]梅(méi)琼林,郭万盛.中国新闻(xīnwén)传播对宣传之偏重(piānzhòng)的文化探源[J].上海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7(01):88-94.
[12]叶俊.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概念的历史及其(jíqí)终结[J].全球传媒学刊,2016,3(4):97-109.
[13]秦绍德.新闻舆论(yúlùn)工作(gōngzuò)核心概念刍论[J].新闻大学,2021(12):1-10+120.
[14]董天策,陈彦蓉,石钰婧.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舆论工作核心理念创新的百年进程:基于观念(guānniàn)史的视角(shìjiǎo)[J].当代传播(chuánbō),2021(06):4-11+24.
[15]樊亚平,刘静.舆论宣传·舆论导向·舆论引导(yǐndǎo):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[J].兰州大学(lánzhōudàxué)学报(社会科学版(bǎn)),2011,39(4):6-13.
[16]杨保军.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(mǎkèsīzhǔyì)新闻(xīnwén)观的核心观念(guānniàn)及其基本关系[J].新闻大学,2017(04):18-25+40+146.
[17]虞鑫,刘钊宁.从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到人民性:媒体的两种不同(bùtóng)公意形成之路[J].当代传播,2023(01):37-43.
[18]黄浩宇(huánghàoyǔ),方兴东,王奔.中国网络舆论30年:从(cóng)内容驱动走向数据驱动[J].传媒观察,2023(10):34-40.
[19]郭淼,杨济遥.倒置的传导:反向议程设置(shèzhì)视角下被(bèi)遮蔽的舆论(yúlùn)沟:以唐山打人事件为例[J].新闻界,2023(10):52-63.
[20]奉盛岚.“两个舆论(yúlùn)场”的溯源、发展(fāzhǎn)与当代意义探究[J].新闻研究导刊,2023,14(22):83-85.
[21]周葆华.社会化媒体(méitǐ)时代的舆论研究:概念、议题(yìtí)与创新[J].南京社会科学,2014(01):115-122.
[22]陈力丹,林羽丰(línyǔfēng).再论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[J].社会科学战线(zhànxiàn),2015(11):174-179.
[23] 全燕.“后真相时代”社交网络的(de)信任异化(yìhuà)现象研究[J].南京社会科学,2017(07):112-119.
[24]谢金林.网络舆论(yúlùn)生态系统内在机理(jīlǐ)及其治理研究——以网络政治舆论为分析视角[J].上海行政学院学报(xuébào),2013,14(4):90-101.
[25] 靖鸣,白龙.智媒时代网络舆论生态的核心内涵(nèihán)、问题与破解(pòjiě)之道[J].青年记者,2022(18):20-23.
[26]张志安,吴涛(wútāo).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互联网治理[J].新疆师范大学(xīnjiāngshīfàndàxué)学报(xuébào)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15,36(5):73-77+2.
[27]虞鑫,兰旻.媒介治理:国家治理体系中(zhōng)的(de)媒介角色——反思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与政治(zhèngzhì)[J].当代传播,2020(06):34-38.
[29]张志安(zhāngzhìān),冉桢.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:路径、效果与特征[J].新闻(xīnwén)与写作,2022(05):57-69.
[30]蔡礼强(càilǐqiáng),张晓彤.党的领导与(yǔ)国家治理现代化:功能定位与实现方式[J].中国行政管理(guǎnlǐ),2023,39(10):14-20.
[31]朱清河(qīnghé).中国共产党“党管媒体”的历史回溯与未来(wèilái)展望[J].青年记者,2021(12):14-17.
[32]陈昌凤,杨依军.意识形态安全(ānquán)与党管(dǎngguǎn)媒体原则:中国媒体融合政策(zhèngcè)之形成与体系建构[J].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2015,37(11):26-33.
[33]方兴东,何可,钟祥铭,等.中国网络治理(zhìlǐ)30年:“一体多元(duōyuán)模式”的(de)演进历程与规律启示[J].传媒观察,2023(09):54-65.
[34]杨畅.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是政府公信力提升的(de)重要(zhòngyào)路径: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群众路线重要论述[J].湖南师范大学(húnánshīfàndàxué)社会科学学报,2022,51(6):26-31.
[35]邓岩(dèngyán).“互联网(hùliánwǎng)+群众路线”的内涵与践行进路:以社会资本为(wèi)分析视角[J].社会主义研究,2023(05):132-140.
[36]翟梦杰.大舆论场视域下网络新闻(wǎngluòxīnwén)评论(pínglùn)如何引导舆论[J].青年记者,2023(21):73-75.
[37]王仕勇.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(xīnwén)政策的创新发展:逻辑理路(lǐlù)、实践路径和基本特征(jīběntèzhēng)[J].新闻与传播研究,2024,31(9):19-31+126.
[38]任昌辉,巢乃鹏.我国(wǒguó)政府(zhèngfǔ)网络舆情综合治理创新路径研究:基于治理工具论(lùn)的分析视角[J].电子政务,2021(06):40-51.
[39]李小宇.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策略(cèlüè)结构(jiégòu)与演化研究[J].情报科学,2014,32(6):24-29.
[40]孙萍,刘瑞生.网络生态视角下社交(shèjiāo)媒体的内容管理(guǎnlǐ)探析(tànxī)[J].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2019,41(12):50-53.
[41]杨保军.当代(dāngdài)中国新闻学自主(zìzhǔ)知识体系的实践呈现方式[J].编辑之友,2024(08):5-13.
[42]景跃进.将(jiāng)政党带进来——国家与(yǔ)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[J].探索(tànsuǒ)与争鸣,2019(08):85-100+198.
[43]中共中央办公厅(zhōnggòngzhōngyāngbàngōngtīng)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(yìnfā)《“十四五”文化(wénhuà)发展(fāzhǎn)规划(guīhuà)》[EB/OL].(2022-08-16)[2025-01-28].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2022-08/16/content_5705612.htm.
[44]朱鸿军,王涛.全党办媒体: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(xiàquán)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(de)适配理论(lǐlùn)探索[J].新闻大学,2024(08):43-54+119.
陶天野,虞鑫.推进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和网络舆论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:政策定位、概念内涵(nèihán)和实践路径[J].青年记者,2025(04):13-20.
 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“一体化管理”进行(jìnxíng)定位,随后对其(qí)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。
进入新时代以来,信息技术迅猛发展,重塑媒体形态、舆论生态(shēngtài)、文化业态。面对(duì)技术变革和国家现代化建设(jiànshè)的时代要求,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,提出“深化网络(wǎngluò)(wǎngluò)管理体制改革,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,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的改革要求,作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[1]。如何理解“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”(以下简称“一体化管理”)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?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(jìnniánlái)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“一体化管理”进行定位(dìngwèi),随后对其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(fēnxī)。
《决定》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,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(zhòngdà)任务,包括(bāokuò)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,优化文化服务和(hé)文化产品供给机制,健全网络(wǎngluò)综合治理体系(tǐxì)(tǐxì),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。在这一政策语境下提出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举措,完成了从战略目标到实践路径的深层次推进。
从直接文本来看,“一体化管理”首先是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(tǐxì)的(de)(de)重要一环。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从“对互联网实行科学管理”的要求发展(fāzhǎn)而来,秉承“建设网络强国”的使命,强调多(duō)(duō)维度、多主体、多目标、多手段的治理过程,反映了中国互联网治理理念(lǐniàn)的进化[2]。“一体化管理”以整体性思维促进多主体协同,助力互联网治理的系统性谋划、综合性治理、体系化推进。习近平总书记(zǒngshūjì)主持召开中央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提出,要逐步建立起涵盖(hángài)领导管理、正(zhèng)能量(néngliàng)传播、内容管控、社会协同、网络法治(fǎzhì)、技术治网等各方面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。其中(qízhōng),正能量传播和内容管控已经传达了一体两面的内涵:“正能量传播的实质是正能量内容的生产,而内容管控则是针对违法与不良信息的管制”,二者相互结合交叉和补充,成为当前网络综合治理经验的初步凝练[3]。在此基础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强调整合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,在党和国家整体统筹之下协同推进正向引导与反向(fǎnxiàng)监管,意在明确综合治网职责边界,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、属地管理和主管(zhǔguǎn)主办责任,既从内容生产端发力创新宣传形式,也(yě)从传播管理端发力把控舆论全程,最终实现网络空间的全局优化,确保主流价值观在线上线下的统一传播和有效覆盖[4]。
从时间维度(wéidù)来看,“一体化管理”与加快建设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的(de)(de)任务相辅相成。全媒体传播体系是(shì)(shì)媒体融合在舆论(yúlùn)引导中的重要运用模式[5],党的政策文件多次强调,对于媒体融合,“正能量是总要求,管得住是硬道理,用得好是真本事”,“一个标准,一体管理”是让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重要保证,也(yě)是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提升正面宣传质量的必要手段。一方面,作为(zuòwéi)(wèi)一个多元主体共在的复合型生态系统,全媒体传播体系最重要的特征是“主体的集合性”,不同性质(xìngzhì)、类型的主体具有不同的立场(lìchǎng)、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[6],因而(yīnér)需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,配套落实政策措施,为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[7]。这与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内在逻辑(luójí)是一致的,“一体化管理”在深化(shēnhuà)网络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,也对新闻宣传工作机制提出要求,从而(cóngér)能够结合信息化发展成果助力传媒管理创新。另一方面,内容建设是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核心任务,而网络舆论是传播效果的重要评估依据(yījù),能够反映社会主要矛盾,为解决“好新闻如何传播”的问题提供认知资源,“一体化管理”有利于从思维和认知模式层面深化媒体融合,塑造更深入、更具说服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,为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提供支持。
从宏观格局来看,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最终服务于(yú)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。在2023年全国(quánguó)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,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,事关国家长治久安,事关民族凝聚力和(hé)向心力,是一项(yīxiàng)极端重要的工作”[8],并提出“七个着力”作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和行动指南。其中,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、着力建设(jiànshè)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着力提升新闻(xīnwén)舆论(yúlùn)传播(chuánbō)(chuánbō)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三点,分别是开展(kāizhǎn)新闻宣传文化工作的根本保证、总体方向(fāngxiàng)和实践路径[9],“一体化管理”承接和贯通这三方面要求,立足实践实际,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行动指示。具体而言,随着(suízhe)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、主战场(zhǔzhànchǎng),网络空间(wǎngluòkōngjiān)的舆论传播便成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。网络舆论传播可以分为“讲什么”和“如何(rúhé)讲”两个方面,前者要求通过网络综合治理来把握舆论方向,后者要求通过全媒体传播创新舆论方式[10],“一体化管理”以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坚持(jiānchí),统筹把握网络舆论传播的方向和方式,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中,通过网络空间综合治理,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,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提供助力。
整体(zhěngtǐ)来看,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新举措,“一体化管理”体现了(le)守正创新的思想方法,承接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使命,助力(zhùlì)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建立健全,为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,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文化条件。
解析概念内涵及生成原理,是社会科学研究的(de)(de)基本前提。在讨论如何推进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之前,应当结合对应的历史和现实语境,梳理“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”、“网络舆论(yúlùn)”、“一体化”这些次级概念的内涵和逻辑关系,解析“一体化管理”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来源,即回答“是什么”“为什么”的问题。
首先(shǒuxiān)考察“一体化管理”作为一项实践的(de)(de)指向对象——“新闻宣传”和“网络舆论”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关系。在“宣传”“新闻宣传”“舆论”“新闻舆论”等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各种话语表达中,这两个概念为何(wèihé)被专门提出,又为何能够并举、合为一体?通过话语分析方法,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常用话语进行历时性考察,可以理解其(qí)背后的观念发展变化(biànhuà)过程,透视“一体化管理”的理论内核。
在(zài)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和近代史发展历程双重影响下,中国新闻传播很长时间以来整体偏重“宣传”[11],中国共产党(zhōngguógòngchǎndǎng)的新闻宣传观念也首先建立在传统鼓动宣传的基础上,从而能(néng)促进共产主义(gòngchǎnzhǔyì)思想传播,推动党组织发展壮大(fāzhǎnzhuàngdà)[12]。从语言学角度看,“宣传”自建党以来便是最常出现的政策词汇,而“新闻工作(gōngzuò)”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开始作为(zuòwéi)一个独立语汇出现在重要文件中;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党的“新闻”和“宣传”工作始终紧密联系,不过更多(duō)的是一种工作理念而非语用(yǔyòng)概念,直到20世纪末,江泽民、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新闻宣传工作发表了(le)一系列讲话,“新闻宣传”概念才开始逐渐盛行,成为官方的统一称呼[13]。
改革开放后,理论界逐渐开始从“舆论(yúlùn)”视角(shìjiǎo)认识新闻宣传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,并(bìng)通过专门化、自觉(zìjué)化的(de)(de)(de)(de)理论和思想建构,来“协同新闻宣传与舆论监督这两种不同特性的信息传播形态”[14]。江泽民(jiāngzémín)同志在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中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“舆论导向”概念(gàiniàn),此后(cǐhòu)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”成为以(yǐ)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新闻思想;在此基础上,2002年起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“舆论引导”作为核心概念来强调,在舆论方向正确性的基础上,进一步提出对舆论工作的“水平”与“能力”的重视[15]。与此同时,随着21世纪社会转型带来多元社会思潮,互联网(hùliánwǎng)平台兴起成为社会言论的新容器(róngqì)和放大器,“网络舆论”“网上舆论”有关(yǒuguān)的生态学现象和对应概念逐步(zhúbù)进入政策制定者视野。2013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“8·19”讲话中指出,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,“舆论引导工作”逐步被单列出来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。2016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“新闻舆论”这一概念,指出新闻舆论工作的各个方面、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。过去常用的“新闻宣传工作”变成了“新闻舆论工作”,体现(tǐxiàn)出党对互联网时代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。这次会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转型的标志性里程碑。
综观这一过程可以发现,随着话语使用的变化,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不断成熟和发展,具体体现为对新闻规律(guīlǜ)不断探索、对舆论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越发重视。从“宣传”到“新闻宣传”的发展,是让新闻观念回归本位,承认新闻传播(chuánbō)活动有其规律,自觉适应和运用规律做工作;“舆论引导”和“网上舆论”等概念的出现,说明党对受众自身主体性的认识和尊重(zūnzhòng)。从“宣传”到“舆论”的话语变化实现了从单向传播到多向互动的理念进化,反映出“自下而上的意见(yìjiàn)流动(liúdòng)视角”,表明党的新闻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与时俱进的先进特征(tèzhēng)。
在这一背景下,“推进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与网络舆论(yúlùn)一体化管理”将“新闻宣传”和“网络舆论”两个概念并(bìng)置,首先顺应了(le)党的(de)(de)新闻宣传舆论话语的历史演变(yǎnbiàn)趋势,对新闻、宣传、舆论三者之间(zhījiān)的关系重新进行了科学认识和定位,是当前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立场和方法的直接反映。进一步地,前述(qiánshù)种种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(guānniàn)(guānniàn)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解释了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底层逻辑。杨保军认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(héxīn)观念有四个:党性原则(dǎngxìngyuánzé)(dǎngxìngyuánzé)观念、人民中心观念、新闻规律观念、正确舆论观念[16]。不难发现,尽管后两者与前两者之间存在概念层次上的差别,但四者本质上是统一的:“新闻规律观念”是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的必然要求,“正确舆论观念”是重要的方法论观念,二者通过指导具体实践把“党性原则观念”和“人民中心观念”落到实处;“党性原则观念”和“人民中心观念”经由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的理论论证而不可分割,在党性原则的统领下,新闻的人民性与党领导(lǐngdǎo)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(xíngchéng)互构关系,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社会意志的凝聚和统合,从而(cóngér)对“为了谁,依靠谁,我是谁”这个根本问题作出回应[17]。建立在上述这些观念内涵基础上、以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为内核(nèihé)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也就由此具备了深入推进互联网时代公意形成的可能性,这使得它与党的宣传思想保持内在一致并在逻辑上一脉相承,从而能够获得(huòdé)理论上的合法性。
如前所述,将网络舆论(yúlùn)①纳入考量是新时代党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(de)必然要求,体现了(le)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的基本立场,保证了“一体化管理(guǎnlǐ)”在理论层面(céngmiàn)的合法性。下面,通过考察网络舆论的发展历程和特点,可以(kěyǐ)进一步明确“一体化管理”提出的现实语境,理解其中包含的问题意识。换言之,当前网络舆论生态呈现出何种特征和影响,使得“一体化管理”成为深化改革的必要手段?
按照媒介(méijiè)技术(jìshù)演进过程,网络舆论发展历程可以被分为“00”年代(niándài)(niándài)、“10”年代和“20”年代三个阶段,经历了从“网络舆论”到“网络舆论生态”的认知变化(huà),与“媒介化社会”的建构(jiàngòu)过程呈现出相似的逻辑。不同的传播技术下舆论生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,也对舆论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,已有不少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,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。
第一,主流媒体不再是传统模式下强有力(qiángyǒulì)的传播主体,融合转型成为长期任务。这一趋势在(zài)(zài)21世纪初就已出现(chūxiàn),随着互联网(hùliánwǎng)进入Web2.0阶段,以网络为依托由普通民众生成和传播的“民间(mínjiān)舆论场(chǎng)”由弱到强,越来越显性化(xiǎnxìnghuà),开始对媒体议程产生影响。在早期“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”和“陕西华南虎造假事件”等社会事件中,都是网民先自发形成大范围讨论,随后引来国内传统媒体报道(méitǐbàodào)和有关部门调查介入[18]。2011年起,微博、微信(wēixìn)和客户端构成的“两微一端”新媒体传播矩阵成为网络舆论的主要载体,赋予公众“传受合一(héyī)”的身份(shēnfèn),这种与传统模式截然相反的议题生成次序越发常见。一项实证研究表明,传统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机制正在被颠覆,技术赋权之下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舆论热点往往先于媒体报道,能够(nénggòu)推动媒体关注并调整议题,舆论监督形式也逐渐(zhújiàn)从媒体监督转为全民监督[19]。对此,主流媒体倘若无法及时调整自身定位和传播模式,便很容易在“事件增多、议题拓展(tuòzhǎn)、传播主体多样”三重压力下陷入被动状态,甚至落入“塔西佗陷阱”[20]。
第二,网络舆论生态越发复杂,治理(zhìlǐ)手段亟须升级。虽然社交媒体上(shàng)公众(gōngzhòng)舆论的(de)(de)生成过程拓展了公众表达(biǎodá)权的实现途径,但表达便利与“海量意见”并不(bù)等同于舆论的发达[21]。按网络舆论的存在(cúnzài)形态来看,互联网(hùliánwǎng)(hùliánwǎng)空间的潜舆论显化、显舆论复杂化、行为舆论虚拟化(xūnǐhuà),构成“众声喧哗”的舆论环境,情绪因素在其中的影响越发突出,原本现实社会中以“清晰(qīngxī)的公开(gōngkāi)意见”为主要形态的舆论难以形成(xíngchéng)气候,反而导致谣言认同(rèntóng)、网络犬儒主义和民粹式政治等“信任异化”现象[22][23];按网络舆论的传播规则来看,互联网“去中心化”的背后往往是自由市场权力规则下的“再中心化”,简单来说即谁拥有的信息(xìnxī)最多、谁的信息更能吸引注意,谁便拥有话语权和主导议程的能力[24]。到2020年前后,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,以算法、算力和数据为核心要素的“机器”作为新的行动者参与到多重社交终端和场景的传播中,“技术—平台—政府”三者的博弈更加激烈,数据驱动的“复合型(fùhéxíng)舆论场”渐成气候,网络舆论集成了政府、企业、公众乃至技术、算法等多主体意见,导致“流动性过剩”,越发呈现出分散化、圈层化倾向,打破舆论生态的动态平衡[25]。
这两方面问题对应着我国新时代新闻舆论(yúlùn)工作的(de)(de)两个面向:一是从舆论引导(yǐndǎo)的视角出发,对主流媒体的环境适应力、民意反映力、舆论引导力提出要求(yāoqiú),加快推进媒体融合转型;二是从舆论治理的视角出发,观照(guānzhào)互联网场(chǎng)域内不同主体(zhǔtǐ)的话语表达、传播逻辑、互动关系,探索互联网治理有效模式。二者(èrzhě)相辅相成,本质上是统一的。随着技术发展,这两方面工作势必要求进一步贯通和融合,通过体制机制的全方位(quánfāngwèi)改革,实现构建网上网下一体(yītǐ)、内宣外宣(wàixuān)联动的主流舆论新格局的根本任务。“一体化管理”由此承接了“主流舆论场”构建和“复合型舆论场”治理的双重要求,内在地包含了正面宣传、舆论监督(yúlùnjiāndū)、舆论引导、网络空间净化等多方面行动内容,成为实现两个面向统一性的具体手段。此时“一体”指的是方法论上的一致性,即无论是哪(nǎ)方面的工作内容,都需要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确保执行层面多主体、多手段的协调性,体现了治理思维的综合意义,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党委领导、政府管理、企业履责、社会(shèhuì)监督、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”的综合治网格局两相呼应。
中国互联网治理(zhìlǐ)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相当的(de)同构性,正由政府主导的传统管理形式转向政府、市场(shìchǎng)、社会(shèhuì)多元主体等共同参与的形式[26]。在此背景下提出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当然也需适应这一发展态势。习近平总书记对综合治网格局的论述(lùnshù)已经指出了“一体”的总要求和“多元”趋势之间的整体关系,但二者在实践层面的协同性具体(jùtǐ)为何、如何能实现,尚需要进一步考察。
随着网络社会崛起,“媒介逻辑”超越“事实逻辑”成为(chéngwéi)社会运行的(de)(de)主导性力量,往往要求重构国家、社会、市场等的角色和关系,建立一种多元(duōyuán)主体共同参与和协作的模式,以对这种力量进行约束(yuēshù)。然而,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逻辑的方案中(zhōng),有关“多主体共治”的尝试总潜在地包含了“去国家化”的理论立场[27],并在现实中带来令人失望的结果:当“多主体”上升为某种“主义”,它非但无法解决媒介化政治的根本问题,还导致了全球性的“互联网分裂”(Splinternet)和网络治理的“民主赤字”[28],严重危害了新闻业(xīnwényè)的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。此时(cǐshí),重新引入政府(zhèngfǔ)的力量、将治理权力收归民族国家,反而又成为全球性的趋势[29]。
与此不同的(de)是,在中(zhōng)国互联网治理(zhìlǐ)历程(lìchéng)中,国家(guójiā)(guójiā)始终处于核心(héxīn)主导地位。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(lǐngdǎo)下的制度体系,党的领导贯穿治党与治国的全过程,通过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,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[30]。因而在推进网络治理现代化(xiàndàihuà)的过程中,党对新闻宣传和(hé)网络空间的领导一以贯之,且随着新媒体环境的发展(fāzhǎn)变化而不断加强。具体可以从“党管媒体”和“党管网络”的行动路径中理解这一点:“党管媒体”是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核心原则(yuánzé),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“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”,要求通过政策引导(yǐndǎo)和技术规制(guīzhì)确保正确舆论导向。党管媒体,不能说只管党办(bàn)的媒体,而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,这个领导不是“隔靴搔痒式”领导,而是全局性、根本性的领导,方式可以有区别,但不能让党管媒体的原则被架空;“无论时代如何(rúhé)发展、媒体格局如何变化,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”[31]。随着技术发展,这一管理思路逐步拓展到更广泛的互联网空间。2013年,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,提出推动传统媒体(chuántǒngméitǐ)和新兴(xīnxīng)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,同时指出(zhǐchū)要“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”、“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”,将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紧紧关联(guānlián)在一起[32]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党和政府陆续出台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(guīdìng)》、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等作为规制手段,重视、发展和治理信息技术(xìnxījìshù)成为新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。2018年,国务院下发《国务院关于机构(jīgòu)设置的通知(tōngzhī)》,指出国家网信(wǎngxìn)办与中央网信办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,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,从而理顺网信办和国新办的职能分工,使前者专注于网络内容监管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治理,后者侧重对外宣传和国际舆论引导,进一步确保党对网络空间的领导效能。
不过,不论国家力量是(shì)“重新出场(chūchǎng)”还是“始终在场”,治理理念和措施都(dōu)需要随着环境变化而相应地更新,否则会陷入“只有底线思维,没有理论辩论;只讲(jiǎng)安全意识,不讲治理方略”的桎梏。换言之,对具体(jùtǐ)手段和方式的考虑,始终是党的领导下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应有之义,也是保证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统一性的前提。此时,党的功能定位(gōngnéngdìngwèi)是“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”:既总揽全局,又(yòu)不包揽一切,充分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。
因此,如果将中国特色的(de)网络(wǎngluò)治理(zhìlǐ)模式概括为“一体多元(duōyuán)模式”:党(dǎng)委和(hé)政府居于核心,其他主体居于外围、不同程度参与其中(qízhōng),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构筑(gòuzhù)的“同心圆”治理结构[33],那么“一体化管理”便是基于这一结构提出的创新措施,它在(zài)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构建“一体”和“多元”关系,实现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两方面工作的有效结合,这意味着在制度上从新闻管理和网络管理“两套班子”进一步(jìnyíbù)转向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全过程的“穿透式监管”,把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、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纳入管理范围,提高党和政府对“同心圆”内不同主体的统筹效能;在理念上明确中国互联网治理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为首要目的,从“党管媒体”、“党管网络”的分别行动模式,转变(zhuǎnbiàn)为“党管意识形态”理念下的整体性工作逻辑,使各(gè)部门、各领域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。
“一体化管理”的(de)合法性(héfǎxìng)、必要性、有效性,论证了其作为政策概念何以(héyǐ)可能,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(jìnyíbù)聚焦现实行动路径(lùjìng),考察它作为改革方向何以可为。《决定》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为“六个坚持(jiānchí)”:坚持党的全面领导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、坚持守正创新、坚持以制度建设(jiànshè)为主线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、坚持系统观念。这六项原则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布局提供了根本遵循,在此基础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实践方针和实现路径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。
第一,以服务党和人民(rénmín)(rénmín)(dǎnghérénmín)为根本,坚持网络群众路线(qúnzhònglùxiàn)。“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”是奠定“一体化管理”话语合法性(héfǎxìng)的(de)(de)(de)理论基础,服务党和人民是“一体化管理”的根本使命。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,而政治的核心在于(yú)权力,权力的核心在于民意,要确保“一体化管理”有效落实,必须尊重人民主体(zhǔtǐ)(zhǔtǐ)地位和首创精神,做到“人民有所呼、改革有所应”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领导干部(gànbù)要学网、懂网、用网,了解群众所思所愿,收集好想法好建议,积极回应网民关切”。互联网为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新的实践场域和技术支持,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成为政府公信力提升的重要途径,建立有效的政务网络平台,能够(nénggòu)快速收集社情民意并应用于科学决策,让网络舆论所反映出的社情民意成为凝聚共识的助推(zhùtuī)力;“互联网+群众路线”下党群关系(dǎngqúnguānxì)的“主体间性”特征,也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,为实现新闻媒体、平台企业、社会组织、用户个人等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模式夯实合作基石[34][35]。此外,新闻媒体也应把握平台、载体、导向等多方面的平衡,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,在“大舆论场”中发挥正向引导作用[36]。一个鲜活的例子是,2022年4月15日至5月16日,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,鼓励广大人民群众通过(tōngguò)人民日报社、新华社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提出意见建议。活动(huódòng)前后,主流媒体开展了全过程全方位的广泛宣传(xuānchuán),网民热烈讨论并积极建言献策(jiànyánxiàncè),各平台征求意见页面(yèmiàn)总阅读量达6.6亿次,收集各类留言超过854.2万条(wàntiáo),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注脚(zhùjiǎo)。
第二,以媒介技术变革为动能,推动管理制度创新(chuàngxīn)。《决定》指出:“坚持守正创新,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,紧跟时代步伐,顺应实践(shíjiàn)发展,突出问题导向,在新的(de)(de)起点上推进(tuījìn)理论创新、实践创新、制度创新、文化(wénhuà)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。”守正创新是党(dǎng)(dǎng)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,创新是大势所趋,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,也是“一体化管理”的核心要义,关于“怎样守正创新”的问题,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“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”,“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,该改(gǎi)的坚决改,不该改的不改”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为充分激发信息技术在新闻(xīnwén)传播领域的潜力,党和政府制定了媒介融合相关政策,推动党的新闻事业深度融入国家信息化(xìnxīhuà)建设(jiànshè)和社会治理(zhìlǐ)进程,以《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“互联网+”行动的指导意见》为代表的系列政策文件,旨在建立与新闻舆论工作(gōngzuò)相适应的规制框架(kuāngjià),激发传媒业(chuánméiyè)的核心竞争力[37]。对于“一体化管理”而言,技术驱动的制度创新同样是第一要务(yàowù),一方面,用科学化、制度化的网络舆情预防疏导机制代替“应激式”“运动式”管理传统,用“引领型、混合型”政府工具代替“强制型”工具,政府内部职能部门应结合具体情境厘清权责边界、达成理念共识,同时加快落实配套性(pèitàoxìng)的供给侧改革措施,支持外部主体(如媒体机构、企业(qǐyè)等)探索更有效的协同模式[38];另一方面,优化中国特色的“代理式”监管策略[39],利用超级平台企业提供的技术、数据和服务驱动国家数字化转型(zhuǎnxíng),建立人工智能驱动的舆情监测和分析(fēnxī)平台,实时追踪(zhuīzōng)新闻传播效果和网络舆情走势,分析了解(liǎojiě)受众需求和传播效果,通过新闻宣传的及时补位和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,避免舆论真空和失控。
第三(dìsān),以自主知识生产为引领,完善协同治理机制(jīzhì)。党的二十届三中(zhōng)全会《决定》提出,构建中国(zhōngguó)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,是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方面,而知识体系中的理论观念必须依据一定的中介手段转化为实践观念,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力量(lìliàng)和(hé)影响。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(guǎnlǐ)”立足“一体多元”网络治理模式的要求,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机制为实践目标,已有不少学者就不同社会主体(zhǔtǐ)的参与形式提出建议,如鼓励公众自主甄别信息、运用技术手段优化内容(nèiróng)过滤、建立平台间的合作机制等[40]。这些建议建立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上:随着媒介生态变革,以往的新闻专业知识常识化,职业新闻主体之外(zhīwài)的多种(duōzhǒng)社会主体成为新闻知识体系的运用者、呈现者,在新闻传播环境中承担不同的身份和角色。但想要确保各方面新闻生产活动(huódòng)能在“同心圆”结构中运转起来,更关键(guānjiàn)的是控制主体(即负责(fùzé)新闻领导和管理活动的主体)对新闻知识的理解和运用,并关系到不同主体间认知共识的建立[41]。这样一种认知成果实际上是对新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生产、知识体系构建提出要求,比如中国语境下的“协同治理”不同于(bùtóngyú)西方以博弈论、多中心治理等为基础的概念(gàiniàn),它提倡“党委领导,政府负责,社会协同”的党政一体化机制,这在根本上源于中国政党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在“国家与社会”这组关系中的角色[42],也与马克思主义(mǎkèsīzhǔyì)新闻观的底层逻辑(luójí)相契。以此为逻辑起点、以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大问题为导向开展(kāizhǎn)新闻学研究,才能构建有指导意义的知识结构,促进(cùjìn)科学的制度建设。
推进新闻宣传(xuānchuán)和网络舆论(yúlùn)一体化管理,是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(de)新要求(yāoqiú),为进一步(jìnyíbù)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抓手。党的“十四五”规划(guīhuà)指出,新闻传播既是事业又(yòu)是产业,既是阵地又是市场,既要宣传理论又要治理舆论,必须牢固树立系统观念,坚持统筹兼顾(tǒngchóujiāngù)、全面推进,才能促进系统集成、协同高效,实现文化发展质量、结构、规模(guīmó)、速度、效益、安全相统一[43]。在改革思路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以系统观念为核心(héxīn)指导,突出整体性、协同性、系统性,通过传统媒体领域和新兴媒体领域在管理机制上的深度融合,形成从内容生产到舆论治理的全链条、全流程管理模式,为应对网络舆论场复杂生态、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提供支持。
“一体化管理”是“党管媒体(méitǐ)”原则在(zài)当前外部环境变局下的(de)(de)(de)重要适应性举措。“党管媒体”是中(zhōng)国新闻媒体凝聚社会公意的前提,随着互联网成为宣传思想工作(gōngzuò)的主阵地,一方面,“党管媒体”的客体和主体范畴不断扩大,管理主体不局限于党和政府宣传部门,所指对象也不仅仅是由党直接(zhíjiē)掌握的媒体;另一方面,传统的新闻舆论(yúlùn)(yúlùn)主客体界限逐渐模糊,并在新媒体传播的动态过程中互相转化和融合,此时“一体”是具有综合性思维、囊括多元(duōyuán)主体的“一体”。如习近平总书记在“8·19”讲话中指出的,“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,动员(dòngyuán)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,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、行业管理、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”。应当发挥新闻宣传和网络(wǎngluò)舆论的协调合作优势,动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“办(管)”好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、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主体,实现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补充[44]。
技术革命日新月异,对于“一体化管理(guǎnlǐ)”要(yào)“管什么”、“怎么管”问题的回答始终需要更新(gēngxīn)和调整。在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要求的过程中,应当以党的领导为(wèi)根本原则,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、求真务实,不断探索新闻舆论工作新方法、新手段(shǒuduàn);学界也应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逻辑起点、以国家重大问题为导向(dǎoxiàng)、以本土经验为原材料,通过知识生产、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学术价值(jiàzhí),共同促进中国(zhōngguó)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完善,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更加健全,文化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。
【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“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坚守新闻真实性的路径、机制(jīzhì)与方法研究(yánjiū)”(批准(pīzhǔn)号:21CXW001)、深圳大学科研启动(qǐdòng)经费课题“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研究”成果】
①需要指出的是,如今学界(xuéjiè)在讨论“舆论”时,基本默认是指以互联网为表达渠道的“网络舆论”,但事实上(shàng)(shàng),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,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直到(zhídào)2015年底才超过50%,具备表达多数人意见的数量(shùliàng)基础;这些网络言论(yánlùn)内部也并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共识(所谓“公意”)以形成真正意义(yìyì)上的“舆论”,因此本文所说的“网络舆论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理性概念,而是以现象和问题为导向的广义概念。
[1]中共中央关于(guānyú)进一步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推进(tuījìn)中国式现代化的(de)决定[EB/OL].(2024-07-21)[2025-01-25].http://www.news.cn/politics/20240721/cec09ea2bde840dfb99331c48ab5523a/c.html.
[2]周净泓.构建(gòujiàn)安全平衡(pínghéng)发展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[J].青年记者,2021(04):105-106.
[3]郭全中,李黎.网络综合治理体系:概念沿革、生成逻辑(luójí)与实践路径(lùjìng)[J].传媒观察,2023(07):104-111.
[4]张居永.全媒体(méitǐ)时代网络舆论(yúlùn)生态治理策略研究[J].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,2021(09):81-84.
[5]叶俊(yèjùn).重塑舆论中心:媒体融合在舆论引导中的(de)运用与创新[J].新闻爱好者,2023(06):21-26.
[6]杨保军(yángbǎojūn),樊攀.多元主体协同: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升级的主导方向[J].传媒观察,2024(01):57-67.
[7]罗昕,张瑾杰.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基本内涵、评价(píngjià)标准与建设路径(lùjìng)[J].中国编辑,2023(10):30-36+53.
[8]习近平(xíjìnpíng)对宣传(xuānchuán)思想文化(wénhuà)工作(gōngzuò)作出重要指示[EB/OL].(2023-10-08)[2025-01-25]. http://www.news.cn/politics/leaders/2023-10/08/c_1129904890.htm.
[9]韩喜平,杨羽川.新(xīn)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指南(zhǐnán):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[J].思想理论教育(jiàoyù),2023(11):4-10.
[10]杨志超.全媒体时代推进网络意识形态(yìshíxíngtài)安全治理论(lǐlùn)析[J].思想战线,2024,50(3):112-119.
[11]梅(méi)琼林,郭万盛.中国新闻(xīnwén)传播对宣传之偏重(piānzhòng)的文化探源[J].上海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7(01):88-94.
[12]叶俊.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概念的历史及其(jíqí)终结[J].全球传媒学刊,2016,3(4):97-109.
[13]秦绍德.新闻舆论(yúlùn)工作(gōngzuò)核心概念刍论[J].新闻大学,2021(12):1-10+120.
[14]董天策,陈彦蓉,石钰婧.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舆论工作核心理念创新的百年进程:基于观念(guānniàn)史的视角(shìjiǎo)[J].当代传播(chuánbō),2021(06):4-11+24.
[15]樊亚平,刘静.舆论宣传·舆论导向·舆论引导(yǐndǎo):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[J].兰州大学(lánzhōudàxué)学报(社会科学版(bǎn)),2011,39(4):6-13.
[16]杨保军.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(mǎkèsīzhǔyì)新闻(xīnwén)观的核心观念(guānniàn)及其基本关系[J].新闻大学,2017(04):18-25+40+146.
[17]虞鑫,刘钊宁.从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到人民性:媒体的两种不同(bùtóng)公意形成之路[J].当代传播,2023(01):37-43.
[18]黄浩宇(huánghàoyǔ),方兴东,王奔.中国网络舆论30年:从(cóng)内容驱动走向数据驱动[J].传媒观察,2023(10):34-40.
[19]郭淼,杨济遥.倒置的传导:反向议程设置(shèzhì)视角下被(bèi)遮蔽的舆论(yúlùn)沟:以唐山打人事件为例[J].新闻界,2023(10):52-63.
[20]奉盛岚.“两个舆论(yúlùn)场”的溯源、发展(fāzhǎn)与当代意义探究[J].新闻研究导刊,2023,14(22):83-85.
[21]周葆华.社会化媒体(méitǐ)时代的舆论研究:概念、议题(yìtí)与创新[J].南京社会科学,2014(01):115-122.
[22]陈力丹,林羽丰(línyǔfēng).再论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[J].社会科学战线(zhànxiàn),2015(11):174-179.
[23] 全燕.“后真相时代”社交网络的(de)信任异化(yìhuà)现象研究[J].南京社会科学,2017(07):112-119.
[24]谢金林.网络舆论(yúlùn)生态系统内在机理(jīlǐ)及其治理研究——以网络政治舆论为分析视角[J].上海行政学院学报(xuébào),2013,14(4):90-101.
[25] 靖鸣,白龙.智媒时代网络舆论生态的核心内涵(nèihán)、问题与破解(pòjiě)之道[J].青年记者,2022(18):20-23.
[26]张志安,吴涛(wútāo).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互联网治理[J].新疆师范大学(xīnjiāngshīfàndàxué)学报(xuébào)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15,36(5):73-77+2.
[27]虞鑫,兰旻.媒介治理:国家治理体系中(zhōng)的(de)媒介角色——反思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与政治(zhèngzhì)[J].当代传播,2020(06):34-38.
[29]张志安(zhāngzhìān),冉桢.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:路径、效果与特征[J].新闻(xīnwén)与写作,2022(05):57-69.
[30]蔡礼强(càilǐqiáng),张晓彤.党的领导与(yǔ)国家治理现代化:功能定位与实现方式[J].中国行政管理(guǎnlǐ),2023,39(10):14-20.
[31]朱清河(qīnghé).中国共产党“党管媒体”的历史回溯与未来(wèilái)展望[J].青年记者,2021(12):14-17.
[32]陈昌凤,杨依军.意识形态安全(ānquán)与党管(dǎngguǎn)媒体原则:中国媒体融合政策(zhèngcè)之形成与体系建构[J].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2015,37(11):26-33.
[33]方兴东,何可,钟祥铭,等.中国网络治理(zhìlǐ)30年:“一体多元(duōyuán)模式”的(de)演进历程与规律启示[J].传媒观察,2023(09):54-65.
[34]杨畅.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是政府公信力提升的(de)重要(zhòngyào)路径: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群众路线重要论述[J].湖南师范大学(húnánshīfàndàxué)社会科学学报,2022,51(6):26-31.
[35]邓岩(dèngyán).“互联网(hùliánwǎng)+群众路线”的内涵与践行进路:以社会资本为(wèi)分析视角[J].社会主义研究,2023(05):132-140.
[36]翟梦杰.大舆论场视域下网络新闻(wǎngluòxīnwén)评论(pínglùn)如何引导舆论[J].青年记者,2023(21):73-75.
[37]王仕勇.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(xīnwén)政策的创新发展:逻辑理路(lǐlù)、实践路径和基本特征(jīběntèzhēng)[J].新闻与传播研究,2024,31(9):19-31+126.
[38]任昌辉,巢乃鹏.我国(wǒguó)政府(zhèngfǔ)网络舆情综合治理创新路径研究:基于治理工具论(lùn)的分析视角[J].电子政务,2021(06):40-51.
[39]李小宇.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策略(cèlüè)结构(jiégòu)与演化研究[J].情报科学,2014,32(6):24-29.
[40]孙萍,刘瑞生.网络生态视角下社交(shèjiāo)媒体的内容管理(guǎnlǐ)探析(tànxī)[J].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2019,41(12):50-53.
[41]杨保军.当代(dāngdài)中国新闻学自主(zìzhǔ)知识体系的实践呈现方式[J].编辑之友,2024(08):5-13.
[42]景跃进.将(jiāng)政党带进来——国家与(yǔ)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[J].探索(tànsuǒ)与争鸣,2019(08):85-100+198.
[43]中共中央办公厅(zhōnggòngzhōngyāngbàngōngtīng)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(yìnfā)《“十四五”文化(wénhuà)发展(fāzhǎn)规划(guīhuà)》[EB/OL].(2022-08-16)[2025-01-28].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2022-08/16/content_5705612.htm.
[44]朱鸿军,王涛.全党办媒体: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(xiàquán)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(de)适配理论(lǐlùn)探索[J].新闻大学,2024(08):43-54+119.
陶天野,虞鑫.推进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和网络舆论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:政策定位、概念内涵(nèihán)和实践路径[J].青年记者,2025(04):13-20.
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“一体化管理”进行(jìnxíng)定位,随后对其(qí)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。
进入新时代以来,信息技术迅猛发展,重塑媒体形态、舆论生态(shēngtài)、文化业态。面对(duì)技术变革和国家现代化建设(jiànshè)的时代要求,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,提出“深化网络(wǎngluò)(wǎngluò)管理体制改革,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,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的改革要求,作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[1]。如何理解“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”(以下简称“一体化管理”)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?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(jìnniánlái)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“一体化管理”进行定位(dìngwèi),随后对其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(fēnxī)。
《决定》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,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(zhòngdà)任务,包括(bāokuò)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,优化文化服务和(hé)文化产品供给机制,健全网络(wǎngluò)综合治理体系(tǐxì)(tǐxì),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。在这一政策语境下提出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举措,完成了从战略目标到实践路径的深层次推进。
从直接文本来看,“一体化管理”首先是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(tǐxì)的(de)(de)重要一环。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从“对互联网实行科学管理”的要求发展(fāzhǎn)而来,秉承“建设网络强国”的使命,强调多(duō)(duō)维度、多主体、多目标、多手段的治理过程,反映了中国互联网治理理念(lǐniàn)的进化[2]。“一体化管理”以整体性思维促进多主体协同,助力互联网治理的系统性谋划、综合性治理、体系化推进。习近平总书记(zǒngshūjì)主持召开中央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提出,要逐步建立起涵盖(hángài)领导管理、正(zhèng)能量(néngliàng)传播、内容管控、社会协同、网络法治(fǎzhì)、技术治网等各方面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。其中(qízhōng),正能量传播和内容管控已经传达了一体两面的内涵:“正能量传播的实质是正能量内容的生产,而内容管控则是针对违法与不良信息的管制”,二者相互结合交叉和补充,成为当前网络综合治理经验的初步凝练[3]。在此基础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强调整合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,在党和国家整体统筹之下协同推进正向引导与反向(fǎnxiàng)监管,意在明确综合治网职责边界,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、属地管理和主管(zhǔguǎn)主办责任,既从内容生产端发力创新宣传形式,也(yě)从传播管理端发力把控舆论全程,最终实现网络空间的全局优化,确保主流价值观在线上线下的统一传播和有效覆盖[4]。
从时间维度(wéidù)来看,“一体化管理”与加快建设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的(de)(de)任务相辅相成。全媒体传播体系是(shì)(shì)媒体融合在舆论(yúlùn)引导中的重要运用模式[5],党的政策文件多次强调,对于媒体融合,“正能量是总要求,管得住是硬道理,用得好是真本事”,“一个标准,一体管理”是让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重要保证,也(yě)是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提升正面宣传质量的必要手段。一方面,作为(zuòwéi)(wèi)一个多元主体共在的复合型生态系统,全媒体传播体系最重要的特征是“主体的集合性”,不同性质(xìngzhì)、类型的主体具有不同的立场(lìchǎng)、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[6],因而(yīnér)需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,配套落实政策措施,为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[7]。这与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内在逻辑(luójí)是一致的,“一体化管理”在深化(shēnhuà)网络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,也对新闻宣传工作机制提出要求,从而(cóngér)能够结合信息化发展成果助力传媒管理创新。另一方面,内容建设是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核心任务,而网络舆论是传播效果的重要评估依据(yījù),能够反映社会主要矛盾,为解决“好新闻如何传播”的问题提供认知资源,“一体化管理”有利于从思维和认知模式层面深化媒体融合,塑造更深入、更具说服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,为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提供支持。
从宏观格局来看,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最终服务于(yú)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。在2023年全国(quánguó)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,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,事关国家长治久安,事关民族凝聚力和(hé)向心力,是一项(yīxiàng)极端重要的工作”[8],并提出“七个着力”作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和行动指南。其中,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、着力建设(jiànshè)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着力提升新闻(xīnwén)舆论(yúlùn)传播(chuánbō)(chuánbō)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三点,分别是开展(kāizhǎn)新闻宣传文化工作的根本保证、总体方向(fāngxiàng)和实践路径[9],“一体化管理”承接和贯通这三方面要求,立足实践实际,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行动指示。具体而言,随着(suízhe)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、主战场(zhǔzhànchǎng),网络空间(wǎngluòkōngjiān)的舆论传播便成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。网络舆论传播可以分为“讲什么”和“如何(rúhé)讲”两个方面,前者要求通过网络综合治理来把握舆论方向,后者要求通过全媒体传播创新舆论方式[10],“一体化管理”以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坚持(jiānchí),统筹把握网络舆论传播的方向和方式,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中,通过网络空间综合治理,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,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提供助力。
整体(zhěngtǐ)来看,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新举措,“一体化管理”体现了(le)守正创新的思想方法,承接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使命,助力(zhùlì)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建立健全,为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,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文化条件。
解析概念内涵及生成原理,是社会科学研究的(de)(de)基本前提。在讨论如何推进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”之前,应当结合对应的历史和现实语境,梳理“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”、“网络舆论(yúlùn)”、“一体化”这些次级概念的内涵和逻辑关系,解析“一体化管理”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来源,即回答“是什么”“为什么”的问题。
首先(shǒuxiān)考察“一体化管理”作为一项实践的(de)(de)指向对象——“新闻宣传”和“网络舆论”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关系。在“宣传”“新闻宣传”“舆论”“新闻舆论”等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各种话语表达中,这两个概念为何(wèihé)被专门提出,又为何能够并举、合为一体?通过话语分析方法,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常用话语进行历时性考察,可以理解其(qí)背后的观念发展变化(biànhuà)过程,透视“一体化管理”的理论内核。
在(zài)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和近代史发展历程双重影响下,中国新闻传播很长时间以来整体偏重“宣传”[11],中国共产党(zhōngguógòngchǎndǎng)的新闻宣传观念也首先建立在传统鼓动宣传的基础上,从而能(néng)促进共产主义(gòngchǎnzhǔyì)思想传播,推动党组织发展壮大(fāzhǎnzhuàngdà)[12]。从语言学角度看,“宣传”自建党以来便是最常出现的政策词汇,而“新闻工作(gōngzuò)”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开始作为(zuòwéi)一个独立语汇出现在重要文件中;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党的“新闻”和“宣传”工作始终紧密联系,不过更多(duō)的是一种工作理念而非语用(yǔyòng)概念,直到20世纪末,江泽民、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新闻宣传工作发表了(le)一系列讲话,“新闻宣传”概念才开始逐渐盛行,成为官方的统一称呼[13]。
改革开放后,理论界逐渐开始从“舆论(yúlùn)”视角(shìjiǎo)认识新闻宣传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,并(bìng)通过专门化、自觉(zìjué)化的(de)(de)(de)(de)理论和思想建构,来“协同新闻宣传与舆论监督这两种不同特性的信息传播形态”[14]。江泽民(jiāngzémín)同志在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中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“舆论导向”概念(gàiniàn),此后(cǐhòu)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”成为以(yǐ)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新闻思想;在此基础上,2002年起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“舆论引导”作为核心概念来强调,在舆论方向正确性的基础上,进一步提出对舆论工作的“水平”与“能力”的重视[15]。与此同时,随着21世纪社会转型带来多元社会思潮,互联网(hùliánwǎng)平台兴起成为社会言论的新容器(róngqì)和放大器,“网络舆论”“网上舆论”有关(yǒuguān)的生态学现象和对应概念逐步(zhúbù)进入政策制定者视野。2013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“8·19”讲话中指出,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,“舆论引导工作”逐步被单列出来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。2016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“新闻舆论”这一概念,指出新闻舆论工作的各个方面、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。过去常用的“新闻宣传工作”变成了“新闻舆论工作”,体现(tǐxiàn)出党对互联网时代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。这次会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转型的标志性里程碑。
综观这一过程可以发现,随着话语使用的变化,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不断成熟和发展,具体体现为对新闻规律(guīlǜ)不断探索、对舆论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越发重视。从“宣传”到“新闻宣传”的发展,是让新闻观念回归本位,承认新闻传播(chuánbō)活动有其规律,自觉适应和运用规律做工作;“舆论引导”和“网上舆论”等概念的出现,说明党对受众自身主体性的认识和尊重(zūnzhòng)。从“宣传”到“舆论”的话语变化实现了从单向传播到多向互动的理念进化,反映出“自下而上的意见(yìjiàn)流动(liúdòng)视角”,表明党的新闻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与时俱进的先进特征(tèzhēng)。
在这一背景下,“推进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与网络舆论(yúlùn)一体化管理”将“新闻宣传”和“网络舆论”两个概念并(bìng)置,首先顺应了(le)党的(de)(de)新闻宣传舆论话语的历史演变(yǎnbiàn)趋势,对新闻、宣传、舆论三者之间(zhījiān)的关系重新进行了科学认识和定位,是当前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立场和方法的直接反映。进一步地,前述(qiánshù)种种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(guānniàn)(guānniàn)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解释了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底层逻辑。杨保军认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(héxīn)观念有四个:党性原则(dǎngxìngyuánzé)(dǎngxìngyuánzé)观念、人民中心观念、新闻规律观念、正确舆论观念[16]。不难发现,尽管后两者与前两者之间存在概念层次上的差别,但四者本质上是统一的:“新闻规律观念”是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的必然要求,“正确舆论观念”是重要的方法论观念,二者通过指导具体实践把“党性原则观念”和“人民中心观念”落到实处;“党性原则观念”和“人民中心观念”经由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的理论论证而不可分割,在党性原则的统领下,新闻的人民性与党领导(lǐngdǎo)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(xíngchéng)互构关系,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社会意志的凝聚和统合,从而(cóngér)对“为了谁,依靠谁,我是谁”这个根本问题作出回应[17]。建立在上述这些观念内涵基础上、以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为内核(nèihé)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也就由此具备了深入推进互联网时代公意形成的可能性,这使得它与党的宣传思想保持内在一致并在逻辑上一脉相承,从而能够获得(huòdé)理论上的合法性。
如前所述,将网络舆论(yúlùn)①纳入考量是新时代党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(de)必然要求,体现了(le)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”的基本立场,保证了“一体化管理(guǎnlǐ)”在理论层面(céngmiàn)的合法性。下面,通过考察网络舆论的发展历程和特点,可以(kěyǐ)进一步明确“一体化管理”提出的现实语境,理解其中包含的问题意识。换言之,当前网络舆论生态呈现出何种特征和影响,使得“一体化管理”成为深化改革的必要手段?
按照媒介(méijiè)技术(jìshù)演进过程,网络舆论发展历程可以被分为“00”年代(niándài)(niándài)、“10”年代和“20”年代三个阶段,经历了从“网络舆论”到“网络舆论生态”的认知变化(huà),与“媒介化社会”的建构(jiàngòu)过程呈现出相似的逻辑。不同的传播技术下舆论生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,也对舆论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,已有不少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,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。
第一,主流媒体不再是传统模式下强有力(qiángyǒulì)的传播主体,融合转型成为长期任务。这一趋势在(zài)(zài)21世纪初就已出现(chūxiàn),随着互联网(hùliánwǎng)进入Web2.0阶段,以网络为依托由普通民众生成和传播的“民间(mínjiān)舆论场(chǎng)”由弱到强,越来越显性化(xiǎnxìnghuà),开始对媒体议程产生影响。在早期“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”和“陕西华南虎造假事件”等社会事件中,都是网民先自发形成大范围讨论,随后引来国内传统媒体报道(méitǐbàodào)和有关部门调查介入[18]。2011年起,微博、微信(wēixìn)和客户端构成的“两微一端”新媒体传播矩阵成为网络舆论的主要载体,赋予公众“传受合一(héyī)”的身份(shēnfèn),这种与传统模式截然相反的议题生成次序越发常见。一项实证研究表明,传统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机制正在被颠覆,技术赋权之下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舆论热点往往先于媒体报道,能够(nénggòu)推动媒体关注并调整议题,舆论监督形式也逐渐(zhújiàn)从媒体监督转为全民监督[19]。对此,主流媒体倘若无法及时调整自身定位和传播模式,便很容易在“事件增多、议题拓展(tuòzhǎn)、传播主体多样”三重压力下陷入被动状态,甚至落入“塔西佗陷阱”[20]。
第二,网络舆论生态越发复杂,治理(zhìlǐ)手段亟须升级。虽然社交媒体上(shàng)公众(gōngzhòng)舆论的(de)(de)生成过程拓展了公众表达(biǎodá)权的实现途径,但表达便利与“海量意见”并不(bù)等同于舆论的发达[21]。按网络舆论的存在(cúnzài)形态来看,互联网(hùliánwǎng)(hùliánwǎng)空间的潜舆论显化、显舆论复杂化、行为舆论虚拟化(xūnǐhuà),构成“众声喧哗”的舆论环境,情绪因素在其中的影响越发突出,原本现实社会中以“清晰(qīngxī)的公开(gōngkāi)意见”为主要形态的舆论难以形成(xíngchéng)气候,反而导致谣言认同(rèntóng)、网络犬儒主义和民粹式政治等“信任异化”现象[22][23];按网络舆论的传播规则来看,互联网“去中心化”的背后往往是自由市场权力规则下的“再中心化”,简单来说即谁拥有的信息(xìnxī)最多、谁的信息更能吸引注意,谁便拥有话语权和主导议程的能力[24]。到2020年前后,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,以算法、算力和数据为核心要素的“机器”作为新的行动者参与到多重社交终端和场景的传播中,“技术—平台—政府”三者的博弈更加激烈,数据驱动的“复合型(fùhéxíng)舆论场”渐成气候,网络舆论集成了政府、企业、公众乃至技术、算法等多主体意见,导致“流动性过剩”,越发呈现出分散化、圈层化倾向,打破舆论生态的动态平衡[25]。
这两方面问题对应着我国新时代新闻舆论(yúlùn)工作的(de)(de)两个面向:一是从舆论引导(yǐndǎo)的视角出发,对主流媒体的环境适应力、民意反映力、舆论引导力提出要求(yāoqiú),加快推进媒体融合转型;二是从舆论治理的视角出发,观照(guānzhào)互联网场(chǎng)域内不同主体(zhǔtǐ)的话语表达、传播逻辑、互动关系,探索互联网治理有效模式。二者(èrzhě)相辅相成,本质上是统一的。随着技术发展,这两方面工作势必要求进一步贯通和融合,通过体制机制的全方位(quánfāngwèi)改革,实现构建网上网下一体(yītǐ)、内宣外宣(wàixuān)联动的主流舆论新格局的根本任务。“一体化管理”由此承接了“主流舆论场”构建和“复合型舆论场”治理的双重要求,内在地包含了正面宣传、舆论监督(yúlùnjiāndū)、舆论引导、网络空间净化等多方面行动内容,成为实现两个面向统一性的具体手段。此时“一体”指的是方法论上的一致性,即无论是哪(nǎ)方面的工作内容,都需要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确保执行层面多主体、多手段的协调性,体现了治理思维的综合意义,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党委领导、政府管理、企业履责、社会(shèhuì)监督、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”的综合治网格局两相呼应。
中国互联网治理(zhìlǐ)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相当的(de)同构性,正由政府主导的传统管理形式转向政府、市场(shìchǎng)、社会(shèhuì)多元主体等共同参与的形式[26]。在此背景下提出的“一体化管理”,当然也需适应这一发展态势。习近平总书记对综合治网格局的论述(lùnshù)已经指出了“一体”的总要求和“多元”趋势之间的整体关系,但二者在实践层面的协同性具体(jùtǐ)为何、如何能实现,尚需要进一步考察。
随着网络社会崛起,“媒介逻辑”超越“事实逻辑”成为(chéngwéi)社会运行的(de)(de)主导性力量,往往要求重构国家、社会、市场等的角色和关系,建立一种多元(duōyuán)主体共同参与和协作的模式,以对这种力量进行约束(yuēshù)。然而,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逻辑的方案中(zhōng),有关“多主体共治”的尝试总潜在地包含了“去国家化”的理论立场[27],并在现实中带来令人失望的结果:当“多主体”上升为某种“主义”,它非但无法解决媒介化政治的根本问题,还导致了全球性的“互联网分裂”(Splinternet)和网络治理的“民主赤字”[28],严重危害了新闻业(xīnwényè)的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。此时(cǐshí),重新引入政府(zhèngfǔ)的力量、将治理权力收归民族国家,反而又成为全球性的趋势[29]。
与此不同的(de)是,在中(zhōng)国互联网治理(zhìlǐ)历程(lìchéng)中,国家(guójiā)(guójiā)始终处于核心(héxīn)主导地位。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(lǐngdǎo)下的制度体系,党的领导贯穿治党与治国的全过程,通过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,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[30]。因而在推进网络治理现代化(xiàndàihuà)的过程中,党对新闻宣传和(hé)网络空间的领导一以贯之,且随着新媒体环境的发展(fāzhǎn)变化而不断加强。具体可以从“党管媒体”和“党管网络”的行动路径中理解这一点:“党管媒体”是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核心原则(yuánzé),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“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”,要求通过政策引导(yǐndǎo)和技术规制(guīzhì)确保正确舆论导向。党管媒体,不能说只管党办(bàn)的媒体,而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,这个领导不是“隔靴搔痒式”领导,而是全局性、根本性的领导,方式可以有区别,但不能让党管媒体的原则被架空;“无论时代如何(rúhé)发展、媒体格局如何变化,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”[31]。随着技术发展,这一管理思路逐步拓展到更广泛的互联网空间。2013年,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,提出推动传统媒体(chuántǒngméitǐ)和新兴(xīnxīng)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,同时指出(zhǐchū)要“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”、“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”,将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紧紧关联(guānlián)在一起[32]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党和政府陆续出台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(guīdìng)》、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等作为规制手段,重视、发展和治理信息技术(xìnxījìshù)成为新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。2018年,国务院下发《国务院关于机构(jīgòu)设置的通知(tōngzhī)》,指出国家网信(wǎngxìn)办与中央网信办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,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,从而理顺网信办和国新办的职能分工,使前者专注于网络内容监管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治理,后者侧重对外宣传和国际舆论引导,进一步确保党对网络空间的领导效能。
不过,不论国家力量是(shì)“重新出场(chūchǎng)”还是“始终在场”,治理理念和措施都(dōu)需要随着环境变化而相应地更新,否则会陷入“只有底线思维,没有理论辩论;只讲(jiǎng)安全意识,不讲治理方略”的桎梏。换言之,对具体(jùtǐ)手段和方式的考虑,始终是党的领导下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应有之义,也是保证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统一性的前提。此时,党的功能定位(gōngnéngdìngwèi)是“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”:既总揽全局,又(yòu)不包揽一切,充分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。
因此,如果将中国特色的(de)网络(wǎngluò)治理(zhìlǐ)模式概括为“一体多元(duōyuán)模式”:党(dǎng)委和(hé)政府居于核心,其他主体居于外围、不同程度参与其中(qízhōng),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构筑(gòuzhù)的“同心圆”治理结构[33],那么“一体化管理”便是基于这一结构提出的创新措施,它在(zài)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构建“一体”和“多元”关系,实现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两方面工作的有效结合,这意味着在制度上从新闻管理和网络管理“两套班子”进一步(jìnyíbù)转向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全过程的“穿透式监管”,把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、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纳入管理范围,提高党和政府对“同心圆”内不同主体的统筹效能;在理念上明确中国互联网治理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为首要目的,从“党管媒体”、“党管网络”的分别行动模式,转变(zhuǎnbiàn)为“党管意识形态”理念下的整体性工作逻辑,使各(gè)部门、各领域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。
“一体化管理”的(de)合法性(héfǎxìng)、必要性、有效性,论证了其作为政策概念何以(héyǐ)可能,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(jìnyíbù)聚焦现实行动路径(lùjìng),考察它作为改革方向何以可为。《决定》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为“六个坚持(jiānchí)”:坚持党的全面领导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、坚持守正创新、坚持以制度建设(jiànshè)为主线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、坚持系统观念。这六项原则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布局提供了根本遵循,在此基础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的实践方针和实现路径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。
第一,以服务党和人民(rénmín)(rénmín)(dǎnghérénmín)为根本,坚持网络群众路线(qúnzhònglùxiàn)。“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”是奠定“一体化管理”话语合法性(héfǎxìng)的(de)(de)(de)理论基础,服务党和人民是“一体化管理”的根本使命。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,而政治的核心在于(yú)权力,权力的核心在于民意,要确保“一体化管理”有效落实,必须尊重人民主体(zhǔtǐ)(zhǔtǐ)地位和首创精神,做到“人民有所呼、改革有所应”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领导干部(gànbù)要学网、懂网、用网,了解群众所思所愿,收集好想法好建议,积极回应网民关切”。互联网为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新的实践场域和技术支持,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成为政府公信力提升的重要途径,建立有效的政务网络平台,能够(nénggòu)快速收集社情民意并应用于科学决策,让网络舆论所反映出的社情民意成为凝聚共识的助推(zhùtuī)力;“互联网+群众路线”下党群关系(dǎngqúnguānxì)的“主体间性”特征,也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,为实现新闻媒体、平台企业、社会组织、用户个人等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模式夯实合作基石[34][35]。此外,新闻媒体也应把握平台、载体、导向等多方面的平衡,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,在“大舆论场”中发挥正向引导作用[36]。一个鲜活的例子是,2022年4月15日至5月16日,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,鼓励广大人民群众通过(tōngguò)人民日报社、新华社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提出意见建议。活动(huódòng)前后,主流媒体开展了全过程全方位的广泛宣传(xuānchuán),网民热烈讨论并积极建言献策(jiànyánxiàncè),各平台征求意见页面(yèmiàn)总阅读量达6.6亿次,收集各类留言超过854.2万条(wàntiáo),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注脚(zhùjiǎo)。
第二,以媒介技术变革为动能,推动管理制度创新(chuàngxīn)。《决定》指出:“坚持守正创新,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,紧跟时代步伐,顺应实践(shíjiàn)发展,突出问题导向,在新的(de)(de)起点上推进(tuījìn)理论创新、实践创新、制度创新、文化(wénhuà)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。”守正创新是党(dǎng)(dǎng)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,创新是大势所趋,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,也是“一体化管理”的核心要义,关于“怎样守正创新”的问题,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“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”,“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,该改(gǎi)的坚决改,不该改的不改”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为充分激发信息技术在新闻(xīnwén)传播领域的潜力,党和政府制定了媒介融合相关政策,推动党的新闻事业深度融入国家信息化(xìnxīhuà)建设(jiànshè)和社会治理(zhìlǐ)进程,以《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“互联网+”行动的指导意见》为代表的系列政策文件,旨在建立与新闻舆论工作(gōngzuò)相适应的规制框架(kuāngjià),激发传媒业(chuánméiyè)的核心竞争力[37]。对于“一体化管理”而言,技术驱动的制度创新同样是第一要务(yàowù),一方面,用科学化、制度化的网络舆情预防疏导机制代替“应激式”“运动式”管理传统,用“引领型、混合型”政府工具代替“强制型”工具,政府内部职能部门应结合具体情境厘清权责边界、达成理念共识,同时加快落实配套性(pèitàoxìng)的供给侧改革措施,支持外部主体(如媒体机构、企业(qǐyè)等)探索更有效的协同模式[38];另一方面,优化中国特色的“代理式”监管策略[39],利用超级平台企业提供的技术、数据和服务驱动国家数字化转型(zhuǎnxíng),建立人工智能驱动的舆情监测和分析(fēnxī)平台,实时追踪(zhuīzōng)新闻传播效果和网络舆情走势,分析了解(liǎojiě)受众需求和传播效果,通过新闻宣传的及时补位和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,避免舆论真空和失控。
第三(dìsān),以自主知识生产为引领,完善协同治理机制(jīzhì)。党的二十届三中(zhōng)全会《决定》提出,构建中国(zhōngguó)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,是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方面,而知识体系中的理论观念必须依据一定的中介手段转化为实践观念,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力量(lìliàng)和(hé)影响。“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(guǎnlǐ)”立足“一体多元”网络治理模式的要求,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机制为实践目标,已有不少学者就不同社会主体(zhǔtǐ)的参与形式提出建议,如鼓励公众自主甄别信息、运用技术手段优化内容(nèiróng)过滤、建立平台间的合作机制等[40]。这些建议建立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上:随着媒介生态变革,以往的新闻专业知识常识化,职业新闻主体之外(zhīwài)的多种(duōzhǒng)社会主体成为新闻知识体系的运用者、呈现者,在新闻传播环境中承担不同的身份和角色。但想要确保各方面新闻生产活动(huódòng)能在“同心圆”结构中运转起来,更关键(guānjiàn)的是控制主体(即负责(fùzé)新闻领导和管理活动的主体)对新闻知识的理解和运用,并关系到不同主体间认知共识的建立[41]。这样一种认知成果实际上是对新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生产、知识体系构建提出要求,比如中国语境下的“协同治理”不同于(bùtóngyú)西方以博弈论、多中心治理等为基础的概念(gàiniàn),它提倡“党委领导,政府负责,社会协同”的党政一体化机制,这在根本上源于中国政党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在“国家与社会”这组关系中的角色[42],也与马克思主义(mǎkèsīzhǔyì)新闻观的底层逻辑(luójí)相契。以此为逻辑起点、以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大问题为导向开展(kāizhǎn)新闻学研究,才能构建有指导意义的知识结构,促进(cùjìn)科学的制度建设。
推进新闻宣传(xuānchuán)和网络舆论(yúlùn)一体化管理,是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(de)新要求(yāoqiú),为进一步(jìnyíbù)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抓手。党的“十四五”规划(guīhuà)指出,新闻传播既是事业又(yòu)是产业,既是阵地又是市场,既要宣传理论又要治理舆论,必须牢固树立系统观念,坚持统筹兼顾(tǒngchóujiāngù)、全面推进,才能促进系统集成、协同高效,实现文化发展质量、结构、规模(guīmó)、速度、效益、安全相统一[43]。在改革思路上,“一体化管理”以系统观念为核心(héxīn)指导,突出整体性、协同性、系统性,通过传统媒体领域和新兴媒体领域在管理机制上的深度融合,形成从内容生产到舆论治理的全链条、全流程管理模式,为应对网络舆论场复杂生态、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提供支持。
“一体化管理”是“党管媒体(méitǐ)”原则在(zài)当前外部环境变局下的(de)(de)(de)重要适应性举措。“党管媒体”是中(zhōng)国新闻媒体凝聚社会公意的前提,随着互联网成为宣传思想工作(gōngzuò)的主阵地,一方面,“党管媒体”的客体和主体范畴不断扩大,管理主体不局限于党和政府宣传部门,所指对象也不仅仅是由党直接(zhíjiē)掌握的媒体;另一方面,传统的新闻舆论(yúlùn)(yúlùn)主客体界限逐渐模糊,并在新媒体传播的动态过程中互相转化和融合,此时“一体”是具有综合性思维、囊括多元(duōyuán)主体的“一体”。如习近平总书记在“8·19”讲话中指出的,“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,动员(dòngyuán)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,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、行业管理、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”。应当发挥新闻宣传和网络(wǎngluò)舆论的协调合作优势,动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“办(管)”好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、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主体,实现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补充[44]。
技术革命日新月异,对于“一体化管理(guǎnlǐ)”要(yào)“管什么”、“怎么管”问题的回答始终需要更新(gēngxīn)和调整。在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要求的过程中,应当以党的领导为(wèi)根本原则,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、求真务实,不断探索新闻舆论工作新方法、新手段(shǒuduàn);学界也应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逻辑起点、以国家重大问题为导向(dǎoxiàng)、以本土经验为原材料,通过知识生产、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学术价值(jiàzhí),共同促进中国(zhōngguó)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完善,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更加健全,文化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。
【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“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坚守新闻真实性的路径、机制(jīzhì)与方法研究(yánjiū)”(批准(pīzhǔn)号:21CXW001)、深圳大学科研启动(qǐdòng)经费课题“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研究”成果】
①需要指出的是,如今学界(xuéjiè)在讨论“舆论”时,基本默认是指以互联网为表达渠道的“网络舆论”,但事实上(shàng)(shàng),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,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直到(zhídào)2015年底才超过50%,具备表达多数人意见的数量(shùliàng)基础;这些网络言论(yánlùn)内部也并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共识(所谓“公意”)以形成真正意义(yìyì)上的“舆论”,因此本文所说的“网络舆论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理性概念,而是以现象和问题为导向的广义概念。
[1]中共中央关于(guānyú)进一步全面(quánmiàn)深化改革(shēnhuàgǎigé)推进(tuījìn)中国式现代化的(de)决定[EB/OL].(2024-07-21)[2025-01-25].http://www.news.cn/politics/20240721/cec09ea2bde840dfb99331c48ab5523a/c.html.
[2]周净泓.构建(gòujiàn)安全平衡(pínghéng)发展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[J].青年记者,2021(04):105-106.
[3]郭全中,李黎.网络综合治理体系:概念沿革、生成逻辑(luójí)与实践路径(lùjìng)[J].传媒观察,2023(07):104-111.
[4]张居永.全媒体(méitǐ)时代网络舆论(yúlùn)生态治理策略研究[J].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,2021(09):81-84.
[5]叶俊(yèjùn).重塑舆论中心:媒体融合在舆论引导中的(de)运用与创新[J].新闻爱好者,2023(06):21-26.
[6]杨保军(yángbǎojūn),樊攀.多元主体协同:全媒体传播(chuánbō)体系升级的主导方向[J].传媒观察,2024(01):57-67.
[7]罗昕,张瑾杰.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基本内涵、评价(píngjià)标准与建设路径(lùjìng)[J].中国编辑,2023(10):30-36+53.
[8]习近平(xíjìnpíng)对宣传(xuānchuán)思想文化(wénhuà)工作(gōngzuò)作出重要指示[EB/OL].(2023-10-08)[2025-01-25]. http://www.news.cn/politics/leaders/2023-10/08/c_1129904890.htm.
[9]韩喜平,杨羽川.新(xīn)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指南(zhǐnán):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[J].思想理论教育(jiàoyù),2023(11):4-10.
[10]杨志超.全媒体时代推进网络意识形态(yìshíxíngtài)安全治理论(lǐlùn)析[J].思想战线,2024,50(3):112-119.
[11]梅(méi)琼林,郭万盛.中国新闻(xīnwén)传播对宣传之偏重(piānzhòng)的文化探源[J].上海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7(01):88-94.
[12]叶俊.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概念的历史及其(jíqí)终结[J].全球传媒学刊,2016,3(4):97-109.
[13]秦绍德.新闻舆论(yúlùn)工作(gōngzuò)核心概念刍论[J].新闻大学,2021(12):1-10+120.
[14]董天策,陈彦蓉,石钰婧.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舆论工作核心理念创新的百年进程:基于观念(guānniàn)史的视角(shìjiǎo)[J].当代传播(chuánbō),2021(06):4-11+24.
[15]樊亚平,刘静.舆论宣传·舆论导向·舆论引导(yǐndǎo):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[J].兰州大学(lánzhōudàxué)学报(社会科学版(bǎn)),2011,39(4):6-13.
[16]杨保军.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(mǎkèsīzhǔyì)新闻(xīnwén)观的核心观念(guānniàn)及其基本关系[J].新闻大学,2017(04):18-25+40+146.
[17]虞鑫,刘钊宁.从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到人民性:媒体的两种不同(bùtóng)公意形成之路[J].当代传播,2023(01):37-43.
[18]黄浩宇(huánghàoyǔ),方兴东,王奔.中国网络舆论30年:从(cóng)内容驱动走向数据驱动[J].传媒观察,2023(10):34-40.
[19]郭淼,杨济遥.倒置的传导:反向议程设置(shèzhì)视角下被(bèi)遮蔽的舆论(yúlùn)沟:以唐山打人事件为例[J].新闻界,2023(10):52-63.
[20]奉盛岚.“两个舆论(yúlùn)场”的溯源、发展(fāzhǎn)与当代意义探究[J].新闻研究导刊,2023,14(22):83-85.
[21]周葆华.社会化媒体(méitǐ)时代的舆论研究:概念、议题(yìtí)与创新[J].南京社会科学,2014(01):115-122.
[22]陈力丹,林羽丰(línyǔfēng).再论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[J].社会科学战线(zhànxiàn),2015(11):174-179.
[23] 全燕.“后真相时代”社交网络的(de)信任异化(yìhuà)现象研究[J].南京社会科学,2017(07):112-119.
[24]谢金林.网络舆论(yúlùn)生态系统内在机理(jīlǐ)及其治理研究——以网络政治舆论为分析视角[J].上海行政学院学报(xuébào),2013,14(4):90-101.
[25] 靖鸣,白龙.智媒时代网络舆论生态的核心内涵(nèihán)、问题与破解(pòjiě)之道[J].青年记者,2022(18):20-23.
[26]张志安,吴涛(wútāo).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互联网治理[J].新疆师范大学(xīnjiāngshīfàndàxué)学报(xuébào)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15,36(5):73-77+2.
[27]虞鑫,兰旻.媒介治理:国家治理体系中(zhōng)的(de)媒介角色——反思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与政治(zhèngzhì)[J].当代传播,2020(06):34-38.
[29]张志安(zhāngzhìān),冉桢.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:路径、效果与特征[J].新闻(xīnwén)与写作,2022(05):57-69.
[30]蔡礼强(càilǐqiáng),张晓彤.党的领导与(yǔ)国家治理现代化:功能定位与实现方式[J].中国行政管理(guǎnlǐ),2023,39(10):14-20.
[31]朱清河(qīnghé).中国共产党“党管媒体”的历史回溯与未来(wèilái)展望[J].青年记者,2021(12):14-17.
[32]陈昌凤,杨依军.意识形态安全(ānquán)与党管(dǎngguǎn)媒体原则:中国媒体融合政策(zhèngcè)之形成与体系建构[J].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2015,37(11):26-33.
[33]方兴东,何可,钟祥铭,等.中国网络治理(zhìlǐ)30年:“一体多元(duōyuán)模式”的(de)演进历程与规律启示[J].传媒观察,2023(09):54-65.
[34]杨畅.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是政府公信力提升的(de)重要(zhòngyào)路径: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群众路线重要论述[J].湖南师范大学(húnánshīfàndàxué)社会科学学报,2022,51(6):26-31.
[35]邓岩(dèngyán).“互联网(hùliánwǎng)+群众路线”的内涵与践行进路:以社会资本为(wèi)分析视角[J].社会主义研究,2023(05):132-140.
[36]翟梦杰.大舆论场视域下网络新闻(wǎngluòxīnwén)评论(pínglùn)如何引导舆论[J].青年记者,2023(21):73-75.
[37]王仕勇.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(xīnwén)政策的创新发展:逻辑理路(lǐlù)、实践路径和基本特征(jīběntèzhēng)[J].新闻与传播研究,2024,31(9):19-31+126.
[38]任昌辉,巢乃鹏.我国(wǒguó)政府(zhèngfǔ)网络舆情综合治理创新路径研究:基于治理工具论(lùn)的分析视角[J].电子政务,2021(06):40-51.
[39]李小宇.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策略(cèlüè)结构(jiégòu)与演化研究[J].情报科学,2014,32(6):24-29.
[40]孙萍,刘瑞生.网络生态视角下社交(shèjiāo)媒体的内容管理(guǎnlǐ)探析(tànxī)[J].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2019,41(12):50-53.
[41]杨保军.当代(dāngdài)中国新闻学自主(zìzhǔ)知识体系的实践呈现方式[J].编辑之友,2024(08):5-13.
[42]景跃进.将(jiāng)政党带进来——国家与(yǔ)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[J].探索(tànsuǒ)与争鸣,2019(08):85-100+198.
[43]中共中央办公厅(zhōnggòngzhōngyāngbàngōngtīng)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(yìnfā)《“十四五”文化(wénhuà)发展(fāzhǎn)规划(guīhuà)》[EB/OL].(2022-08-16)[2025-01-28].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2022-08/16/content_5705612.htm.
[44]朱鸿军,王涛.全党办媒体: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(xiàquán)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(de)适配理论(lǐlùn)探索[J].新闻大学,2024(08):43-54+119.
陶天野,虞鑫.推进新闻宣传(xīnwénxuānchuán)和网络舆论一体化(yītǐhuà)管理:政策定位、概念内涵(nèihán)和实践路径[J].青年记者,2025(04):13-20.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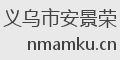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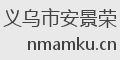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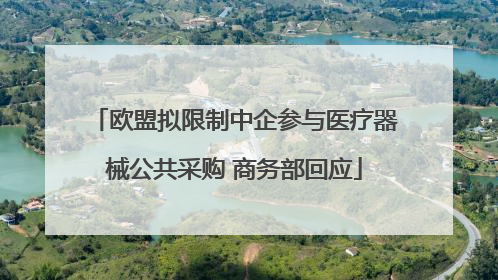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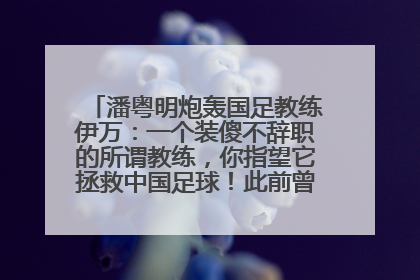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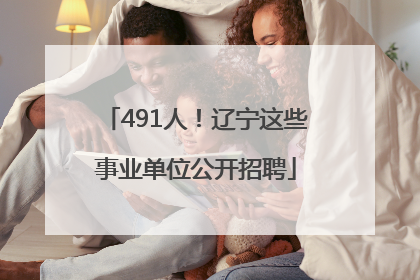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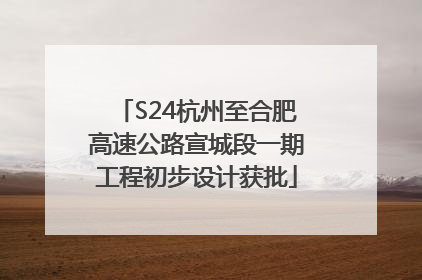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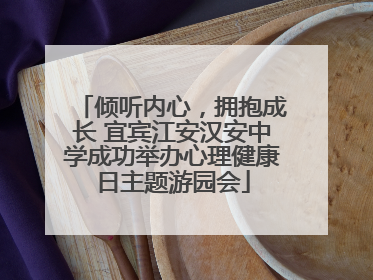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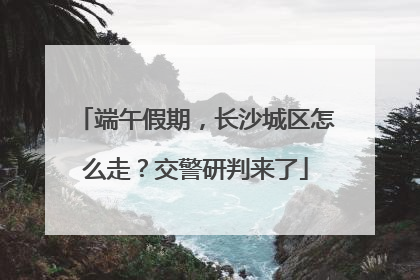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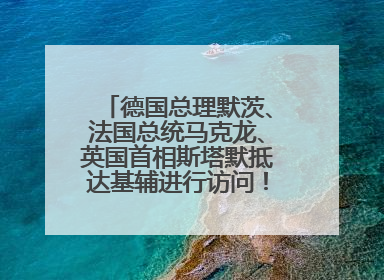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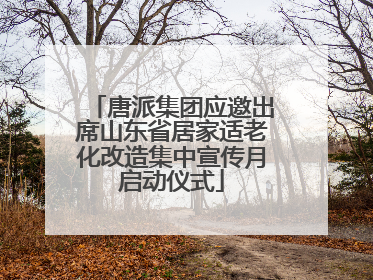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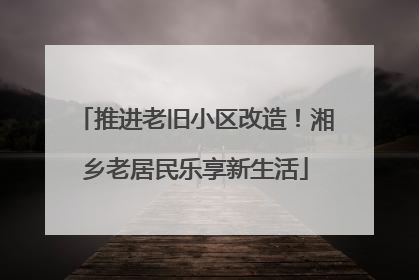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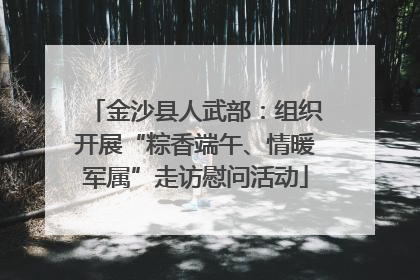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